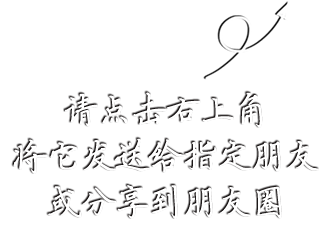江南的冬天多雨,阴冷潮湿,没有雪,但是遍地红叶,象滚烫的南方人的性格。塞北的冬漫长苦寒,初冬时早早下了大雪,然后数月不化,冰封千里,锻造着北方人钢铁般的意志。黄土地上雨雪稀少却是常有的事。每年冬天,这里的人们那份盼雪的心情,最是殷切难遣。
老农们有句谚语:“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一冬下来,若果然能有两三场象模象样的雪,不光农家人乐呵,即如我辈,衣无半缕亲裁,食无一粟自给者,心也将因此而不浮躁,安放在腔子里,静静地、满足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节令已过大雪时,仍然没有一场真正的雪事顾临这片热土。都市的烟尘堵截得人们生气全无,时疫也趁机在人群中做乱。那天气预报说,将有雪!但见连日来彤云密布,寒风阵阵,正是下雪的前兆,于是乎,人们奔走相告:“明天有雪,注意,注意!”
但我是不信的。有关雪的消息,上当总有好几次。十一月初,入冬不久的一个夜晚,我从汾河岸边走过,那里华灯灼照,冷风拂面。忽然有细细的雪粒斜飞而至——呵,下雪了!内心一阵狂喜。哪知未等我走回到家门口,那雪干净儿地停了!第二天早上,地面上干巴巴的,我只疑心我是做了个思念的梦罢。后来断断续续,好几次都是如此情形,说好了有雪,可要么才下便停,要么连影子都不见。阴霾的天,风略吹一吹,黑云四散逃去,脚底灰尘日增月累,只觉得这个老天,真是诓你没商量。
从网上得知,四周的省份都在下雪,只是这里没有。心中失望,整天闷闷的,面上无光,肝火亦旺。虽不至于骂天骂地骂娘,但一腔无名火,无可宣泄处——唉,实在的,爱下不下罢!不等着便是了!本来么,人之所以常怀失望,乃因为轻易相信了,希望了,等着了,才有;若从来都不信,不想往,不苦等,则何处失望去?
没有雪的冬天,温吞吞不冷不热着,所有的树都枯了枝杆,所有的草都焦黑了脸,尘沙散得到处都是,举目萧条,实在无趣。就好比苏堤之春无杨柳,荷塘之夜无明月,黯然销魂,令人情冷。
我虽不再让自己等盼,也不信有雪,但假若老天真降一场豪雪了,我亦不可能置之不理。或者欢呼雀跃,也是自然。
所以,当清晨送走早行的孩子,独自卧回到床上继续贪睡的我,猛抬头看到那方格的窗外,已纷纷扬扬旋舞着雪花时,整个人竟惊跳起来,激动地扑向窗台。
从五楼的高度鸟瞰大地,不知何时,那里已经是皑皑的一片。不能再睡了!我快快地起床,快快洗漱,快快抓起外套,两条腿生了奔跑的冲动。因为太兴奋,所以显得紧张。外套拿起来这件,觉得不妥,又换那件。我想我会一整个上午都呆在雪地里的,必须做好保暖才行。心战栗栗的,颤巍巍的,临出家门,差点遗落了钥匙。
脚步尚可矜持着,心是扑扇着翅膀飞出楼梯间的。粉筛也似的雪粒,兜头兜脸裹将上来,不遮不掩,想落哪里就落哪里。鬓发间,衣襟上,簌簌有声;面颊上,颈子上,触肌生凉。路上积雪,白绒绒的可爱,不很厚,已印着了路人串串足印。
忽觉腹中空空。又怕不吃早饭,不足以抵御这雪天的寒气。路过一家早点摊时,就近拣了个位子,要了豆浆和麻叶。透过碗上腾升的白蒙蒙的热气,看外面琳琅的雪世界,真是快活的场景。
热闹的住宅区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活力,四周充斥着车声,喇叭声,人语声,锅碗勺筷声,一根根麻叶从鼎沸的油锅中滚过的滋滋声……每个人穿得都臃肿,每个人口中都有呼出的白气,白气搅动着白雪,白雪在白气里翩跹,热腾腾,闹哄哄……
简单吃过早点,出东大门往南,步行约二许里,有铁门通汾西公园。公园临汾河而建,西岸浅水区有大片芦荻花。入冬后苇茎枯干了,却仍亭亭立着。今天,我想看一看它们立在风雪中的姿势。
雪落得更加稠密。公园里寂静无人,除了铁丝围栏背后公路上,一辆辆疾驰而过的车子发出的轰鸣声,耳中便只是落雪的声音了。仔细聆听,沙沙,沙沙,可爱无比。平展宽阔的草坪,如今渥了雪,仍有纤细的小刺从白雪中直刺出来,象一柄柄暗青的匕首。我便从这刀丛中走过,笑称自己是刀尖上舞蹈的侠客。众多松树傲然挺立,一簇簇松针,就好象一个个酒杯,每个杯中都盛着晶莹剔透的半盏冰雪。
公园里有一二穿制服的工人在扫雪。沿着芦苇荡修筑的人行道蜿蜒平整,南北通达,一目了然。转眼,我已身在其中。穹高地远,皓白一片,大雪纷飞里,已经看不到对岸那些林立的高楼,只有身前大片的芦苇丛,绵绵延延,一径伸向前方。雪珠子洒将下来,落在苇叶枯梗上,满耳都是唰唰唰的声响,那么清晰,简直震耳。
还没有太多雪挂,苇杆站得很直,近处一两只麻雀栖在上面,啾啁细语。我一向以为,芦荻花迎风的姿态最洒脱,今观雪舞荻花,却又更见风韵了。
很讨厌背后公路上刺耳的车声,那样多的车子象洪水一般哗哗地流走,喧杂声永不衰减,只会递增,有心想忽略,但真的做不到。在这个美丽的地方,美丽的时刻里,它变得尤其使人厌恶了。可惜我没有一根魔棒,挥手之间,让它消遁了罢!
沿着芦苇荡一直向南行去。得意之余,拿出来手机一路狂拍。触屏式手机,不脱掉手套便不能操作。最后,冻到双手通红,竟至僵硬,不堪伸缩之用了。
大雪纷飞,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三国》里面的一个场景:孔明的老泰山黄承彦老人裹着斗篷骑着毛驴在大雪中独行,口内唱着一曲《梁父吟》:“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我站在这里,向天空仰面看去,果然是“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之境。只是我既无驴可骑,亦无桥可度,更无梅可赏,他有“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我只好来个“踏草与扶松,观尽荻花秀”了。
积雪盈寸,雪还在下,天地浑茫一片。走路走到两股战战了,还是舍不得回去。真想就这样一直一直走下去。虽然身上有点冷,但是心里快活,把万事抛转一旁,放怀和天地这样亲近。
若比天地是苇杆,我便是那暂歇了脚步的麻雀,从来没有过的和谐。四周白雪飞扬,我的指爪轻盈,眼神纯粹,但愿我的心,也象那些精灵儿一般——若白纸一张,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