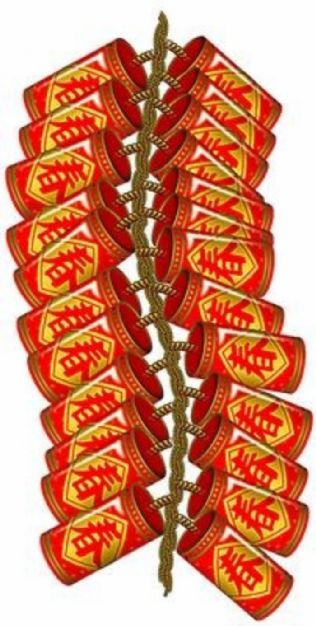



守岁围炉亲情暖
围炉守岁,辞旧迎新。窗外是绽放的烟花,屋内是温暖的炉火,任思绪飘飞在每个动情的瞬间,让记忆掠过沉淀的往事,心底的亲情如潮水涌起……那情,那景,祥和安康,充满温馨。
记得儿时,除夕吃过年夜饭后,一家人围炉而坐,辞岁守岁。土制的火炉上贴有“春”和“福”字,喜气洋洋。守岁时我们都要说几句吉祥话,如“吃红枣,年年好”、“吃年饭,年年赚”等。母亲变戏法似地从挂在屋梁处的竹篮里取出花生、瓜子、糖果等小食品,放进果盘,摆在一张矮方桌上。我心里很纳闷,那个悬挂的竹篮,我曾经站在高凳上把它取下来看过,可里面就是一些食盐、辣椒和香料等,也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把这些零食放进去的。我们嗑着瓜子,吃着香甜的糖果,谈着自己新学期的计划。说笑间,炉火黯淡了下去,母亲便添加一些木炭,火苗又蹿了上来,红红的,暖暖的。
看到我们有些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母亲便让父亲讲故事给我们提神。父亲端起一杯盖碗茶,深深地吸上一口,故事就随着那一缕茶香飘出……对这些不知听了多少遍的故事,我们依然是常听常新。这时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开始密集起来,父亲便给我们发压岁钱,催促着我们去燃放鞭炮,迎接农历新年的钟声。许多年过去了,儿时和父母守岁的情景一直在记忆里萦绕,连同那红红的炉火,温暖了我们清苦而纯真的童年。
年年岁岁,我们回家过年,父母总是与我们一起守岁迎新。去年的除夕夜,春节联欢晚会还没有看到一半,父亲就闭上眼睛打起了盹,母亲给孙辈们发完压岁钱后也是哈欠不断。看到疲倦的父母,我们劝他们回房间休息,不要再坚持守岁了。母亲站起身,伸了伸腰,笑哈哈地说:“没事,喝口浓茶,洗个冷水脸,我们就清醒了。”忽然间,发觉父亲母亲的身体不再如以前健朗,鬓角已有丝丝白发,额头也有几道深深的皱纹。在不知不觉中,父亲母亲老了,而我们这些儿女,却在他们的操劳中成家立业。
默念着“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的诗句,看着日渐衰老的父母,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很心疼他们。我知道,岁月的脚步谁也无法挽留。如今,我最大的祈盼就是在每年的除夕之夜,父亲母亲都能够与我们一起分享那温馨的炉火,一年又一年……
诗中熬年守岁
家,是一个很温暖的字眼儿,因为有家就有守不够的岁月。而除夕,更是把家的氛围渲染到了极致,人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侯鸟般地赶回家中与亲人熬年守岁,图的就是合家欢聚。“守岁围炉竟废眠”,那通宵长明的灯火,既光映着驱赶“百鬼”的民俗,也温存着人们心中积沉已久的亲情。
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的除夕之夜,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篇有关守岁的佳诗丽词,浅咏低诵,真切感人。
守岁,就是熬夜守候“月穷岁尽之日”,迎接农历新年的来临。据古籍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熬年守岁祛邪的习俗。晋代的周处在《风土记》中就写道:“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而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徐君倩则有了一份家的温情,他与妻子一起在除夕守岁,写下了《共内人夜坐守岁》的诗句:“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
到了唐宋,除夕守岁更是盛行,诗人的雅兴激发,从各自的视野对此进行全方位深入细腻的刻画。如孟浩然对人们通宵不寐的描述:“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诗圣杜甫则在《杜位宅守岁》中把除夕守岁这一习俗写得细致生动:“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大文豪苏东坡所写的“儿童强不眠,相守夜喧哗”等著名诗篇,则表现了孩子们除夕守岁时的喧闹场景,将纯真的童趣刻画得栩栩如生。白居易的《客中守岁》是平民百姓人家熬年守岁的写照:“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而皇宫之内、官府之邸、富贵之家,除夕守岁自然是灯光璀璨、惊艳豪华,李世民的《守岁》便甚为耀眼:“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
守岁,“守”的是对旧岁的眷恋之情,“守”的是对新春的憧憬之意。于是,诗人卢同在《守岁》中感叹:“去年留不住,年来也任他。当垆一榼酒,争奈两年何。”;于是,苏东坡在《守岁》中激奋:“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时光飞逝,“守”是守不住的,但愿人们“偏从此夜惜年华”。
年年除夕,岁岁熬年。除夕守岁的民俗连同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守岁诗篇将永远得到传承,因为家的情结,年的韵味始终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