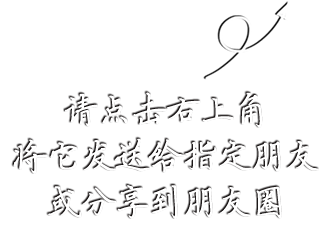他矮小的身材,棕色长裤上满是气象云图,腰间的红色裤带若隐若现,趿拉着一双糊满泥土的懒汉鞋述说着他的邋遢……
老六不是我的亲戚,但我依然得叫他六叔。
老六是村里的一朵奇葩。
流火的六月,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后生们的脊背发红。在这样炎热的日子里,连村口的狗都懒得抬一下眼皮,老六却颇有兴致地在村里溜达。他矮小的身材,久未理过的平头与凌乱的胡渣倒是极其相配的。上身的深蓝色短袖与下身的棕色长裤上满是气象云图,腰间的红色裤带若隐若现,趿拉着一双糊满泥土的懒汉鞋述说着他的邋遢。老六顶着大太阳来到我家院子,憨憨地笑着,我最讨厌的那种笑容,浑身上下都令人生厌。他拿起水瓢舀了满满一瓢水,发出很大的“咕噜”声喝了一半,洒了一半,然后他一抹嘴走了。我撇了撇嘴,心想,腌脏了我那一缸的清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六。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他这样的举动坚持了一个礼拜!
后来,我也常常见到老六。在村里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辆农用三轮车“突突突”地拉着一群人外出。这群人里就有老六,和他的伙计们或站、或坐在三轮车后车兜里,跟随着三轮车的“突突突”声向村外驶去。村人说,他们是去帮人家刮墙、抹腻子粉,他们说,老六人邋遢却不缺钱花,说着意味深长地笑了。有老六的地方,人们就有了调侃的对象,而取笑的内容也大多和他的老婆有关。
比起他的老婆,老六这朵奇葩就要逊色多了。老六的老婆叫东梅,虽说按规矩我们得叫她六婶,可是谁也没有真正叫过她婶儿。每次见到她总是又拎个小包,哪怕是做饭洗衣也包不离身。东梅习惯把自己齐耳的短发烫成烟花状,穿一件紧身外套,内搭一件稍长的毛衣,故意把毛衣的袖子露在外套的外面。及踝的长裙,把袜子筒拉得老高,脚踩5厘米的绑带高跟鞋,左右手腕必须各带一块手表,美美地在大街上溜达。从村西到村东头,村里的小孩总是跟着她屁股后面,边跑边叫着,东梅出来溜达了,快看呐!东梅笑着,走着,仿佛那是她的崇拜者和粉丝团。
村里的事宴上,我总是能看到老六夫妻俩的身影,他们热心地帮忙,做的是最苦最累的营生,即便这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好事者的调侃、嘲讽,两人依然是憨憨地笑着。
突然有一天,老六不在村里晃荡了,也不见了东梅的身影。人们纷纷猜测,好的,坏的,都有,当然更多是调侃。这样的事情更不会有人放在心上。好久,人们才得知了老六瘫痪在床的消息,东梅足不出户,在旁照顾老六。
村人沉默了很久。
忽有一日,老六一直在省城打工的女儿回来了,和东梅一起照顾老六。村人说,老六真是有福啊,有不离不弃的老婆,善良孝顺的女儿,勤奋好学的儿子,是啊,不容易啊。原来老六和东梅是二婚,女儿是东梅带来的,老六对她像是亲生女儿一般。老六和东梅的儿子,据说不久后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