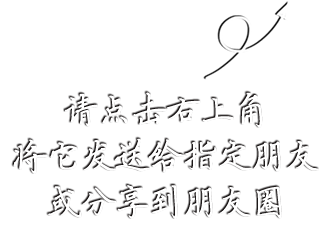图片1
母亲是在二零零七年冬季去世的,距今十七个年头了,一开始难以接受,心里崩溃到了极点,我这个至亲长子经过了好一长段灰色的时刻。那时起,我不再相信什么好人有好报,而是思考为什么好人不长命,为什么母亲这么善良可爱的女性,竟然就在她的虚岁五十八岁时定格了……
在家乡,母亲是以勤劳善良著称的,她的善良品性已经修养成一种品德,乃至升华为当时全村老中青三代人所敬仰的道德,虽然在母亲勤劳持家的时期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任何劳模奖项的评选,但在同时期对母亲有记忆的人当中对她这个无冕模范的头衔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二零零七年的春天没有什么特别,如往年般我们每个家人重温新的一年开始,然后就是气温开始回升了,村里人户外活动多起来。现在回想一下,依稀记得再过一年就是二零零八年,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年轻时的我们大家都对祖国繁荣昌盛充满期待。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国力上升的体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自豪的。家里的情况是父亲在本地政府、企业间表现出色,弟妹二人也有了相当不错的工作,母亲和父亲在早几年搬到了县城,父亲同时给好几家企业做“顾上就问一问”的顾问工作,母亲则在一家单位做勤务工作。
在杨房村就剩我一个长子,我和我的家小留守根据地,那时我已经三十八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纪了。照我在家人面前的倔犟表现,也是到了该独当一面的时候了。
这是个春天的上午,好像春已深,因为阳光已经很热,时分约莫在十点钟左右。记不清当时我在忙些什么,忽然听到院子西边自家的狗在狂吠。[旧时我家的院子西边有一片空地,是父亲买了正房后面邻居家的,当时我家正房有四间,和我家正房平排西面有后邻三间空地,于是父亲经过和邻居协商,通过见证人把那片空地买下来,这片空地现在已经由我一拉通七间盖了正房了。当年由于年久失修,原来的低矮院墙倒塌,和西面墙外的“韩门巷”打通了,街上路过的人可以很容易的进来我家院子,更甚是有几年下雨天,街上道路泥泞,路人图好走就通过我家院子里,然后捷径到村大街(西长安街),呵呵,邻里邻外,也是不好说甚,不能说甚]。听得狗吠得厉害,我急忙跑到西院,只见一个普通出门打扮的大个子男人正站在我家西院朝北方撒尿,见有人来,忙不迭的赔不是。“他妈的”,我怒火填胸,几乎耳光就要扇上去,怒气在胸口翻了几遍,终于压住了,然后呵斥几句,看着那个抄着“太谷家”口音的大个子狼狈地逃去。我莫名的感觉一种恐惧,总觉得好像犯了什么风水,这种感觉却是自从出生还没有过的。
母亲十八九岁就嫁给了父亲,二十岁时生下我,她勤劳善良,手底总有做不完的活。为了家庭,她总是把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当做日常,什么家长里短嚼牙根的事情,她根本就没功夫搭理;东家长西家短,她也没功夫打听,于是她成了杨家公认的好媳妇,邻里共识的好妇女。
用本村人的话讲,我们家是很古怪的家庭,我们家的成员有着固执的性情,各持己见,我们遇事待物有很直接主观的见解思想,不容易被大体所容纳。是那种能独处,不怕寂寞的人,不容易被大体所同化。在过去的农村,这种人是让人们难以理解的,他们直感的觉得,这类人不太普通,只是他们觉不出,我们真的不是太普通的那种人。
只有性情如水的母亲才能融入这样的家庭,才能在这样的家庭里如鱼在水般自由穿梭,创造出生活的活力。
有时候母亲和父亲有些不愉快,娘娘(奶奶)总是诉说父亲的不对,母亲用她如水般的温柔化解家庭的琐碎矛盾,让日常的推进水到渠成地成为生活缩影。她是那般的默默无闻,勤劳付出,用自己的辛苦劳动营造着家庭的安逸。
娘娘对这个儿媳妇是没有半点意见的,母亲是隔在娘娘和父亲之间的调节药,她总是能化解他们母子间的情绪不稳定;大个子的二爷爷作为我们这个家庭的长辈,总是用他充满挑剔的小眼睛直愣愣的看人,特别是在看我和父亲的时候,那是三辈子也不会妥协的挑衅和排斥,反观二爷爷对母亲,姿态也是很和谐的;在外工作的大爷大姑对这个弟媳妇也是没有意见的,他们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笑脸相迎,热饭相待,笑脸相送;同在本村的二姑对母亲更是相当尊敬的,每年二姑家两个孩子的衣服总是母亲帮忙做,表弟表妹对这个妗子的关系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舅舅。邻里邻外男女老幼都佩服这位杨家媳妇,几十年下来,母亲没有和一个邻里红过脸拌过嘴。
母亲用她的平凡创造了不平凡,她用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付出赢得了村人皆知,皆竖拇指。
那个操“太谷家”口音的大个子男人可能是个跑村小商贩,作为男人,出门在外,难免有个急处,避静行个方便,是经常遇着的事,只是那次那样小题大做,却真的少有,也许我对某些事物有些与生俱来的敏锐,产生无师自通的感觉,以至于以后这个念头常常萦绕在心里。院子西北,男子撒尿,每次思想起来,都觉得是一种不详。
记得每年的夏季是母亲最忙碌的季节,小时候我们家的大院子里种了一院的枸杞树,现在约莫记起来有二十来棵的样子。每棵树的大小枝型甚至叶子的大小果实的形状都不同,父亲根据每棵树附近的环境个性的长势给它们修剪了不同的树型,以便能发挥每棵枸杞树最好的优势。其中有几颗长势庞大的树是我们兄妹们很具记忆的,它们不但树体壮、果实大,产量也多。
当时本村院子里种枸杞树的人家也有几家,具体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他们种得很少。当时作为公社所在地,供销社总店就设在我们村,到了秋季就收购晾晒干了的枸杞籽。我们家当时父亲一个人在公社任职,挣的工资也不多,全凭院子里的枸杞树补贴家用。
父亲是善于谋划计策实施计划的那种人,他的脑袋里装满心思,准能发现毛病采取措施什么的。于是日常的生活琐事大部分都落在母亲身上。
母亲的性格里好像从来就不惧什么困难和麻烦,她好像也没有出过什么主意,却是完完全全在履行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和责任。她忠实重复着父亲规划的计划,(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极不安于现实,极爱折腾的人,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家曾经种过七亩的辣椒,种过榆树苗、种过槐树苗、葡萄、果树,虽然我们家九十年代就加入到当时时髦的“万元户”行列,却最终不是财神爷留恋眷顾的那种)。哪怕这些活计根本就做不完,那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其实她的活计也常常是一个人进行的。
种植枸杞树是极其麻烦的,它需要及时的摘下八成熟的果实,然后及时晾晒,以防霉变;却又不能日光直接暴晒,这样干晒的枸杞籽发硬易碎,而且卖的时候没有分量。最佳的方法就是阴晒结合,可是这样的话晾干过程时间过长,有个梅雨天气容易霉烂,父亲思谋出熏干的方法。
在我们家,父亲的想法总是能在第一时间摆上台面搬上桌面,于是在二爷爷鄙夷不屑的目光下,在娘娘止不住唠叨两句的局面下,在母亲的奋力支持下,在我兄妹三人的默默关注下开始进行。主要劳动力是父亲母亲,他们因地制宜把我家当时风道东面的小厨房进行保热处理,又实施秋季切茭箧(高粱杆)劳动,把收集起来的茭箧由母亲做成祭箅,然后在小厨房的屋顶开始熏制枸杞籽,效果是成功的,我们家晾晒出的枸杞籽颜色漂亮,入手温润,味道适口,是供销社收购的典型代表。
只是母亲在炎热的夏季做一日三餐的时候又增添了很多辛苦,炎热的夏季,东屋本来就热,我们每次吃饭都得出一身汗,可怜的母亲不知道为了给家人们做饭流了多少汗水。
母亲的秋季是更加忙碌的,记得有一年,我们家再接再厉,租赁集体的田地,种了七亩的辣椒。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兴起雇人,父亲在实在忙得不可开解的时候出手了。我们在春季开始菅苗的时候雇佣了两个邻居,帮忙菅辣椒苗。秋季如斯,雇佣了几个帮忙摘辣椒的。因为种得多,我家的辣椒采收期特别长,虽然辣椒杆都已收割回院子里,但是一为了不耽误供销社收购期,二又怕堆在一起的辣椒杆霉烂损坏了辣椒质量,采摘辣椒工作必须得愈快愈好,帮忙的邻居们工作时间在,其它时间他们的家中也有活计要干。还是母亲身先士卒,天刚亮就早早起来,一边做饭一边摘辣椒,中午这样,晚上也是。我们兄妹下学后礼拜天也得帮忙。记得当时我们小孩子也是挣钱的,摘一斤多少钱,有时候挣多了,会过日子的母亲就要扣一些,惹起我的不满,父亲及时的兑现。想起父亲当时的讲义气,我还是深有感触。
二零零七年的冬季终于到了,记得每年冬季母亲都是一如既往的忙碌,给我们兄妹三个做新衣服,还有表弟表妹过年的新衣服,打毛线,织毛袜(那个年月没有卖的成绑的毛线,需要妇女们用从生产队里领的棉花或者羊毛自己打毛线)。还得拆洗父亲、娘娘、二爷爷的棉袄棉裤。然后是新年至正月十五的吃喝,都得在腊月二十几时做好。
二零零七那年记得十月十五我村庙会过后不久,一段时间我咳嗽得厉害,去邻村找大夫配了药,五天的药吃了后咳嗽已见好转。
农历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初二,当天天气晴朗,早上院子里有喜鹊在叫,一个毫无预兆甚至略有瑞象的白昼无异常的运行,晚上如常睡下。十一点多时我本以好转的咳嗽忽然爆发,忙不迭的一声接一声的咳嗽把我折腾得坐了起来,又是一阵的急咳,半响,咳嗽稍息,我便睡了下来(当时的我,却是多久后才觉醒,那是我平生最可爱、世界最亲我、给予我生命的母亲——我的妈妈拼尽她生命里乃至宿命里最大最后的力量,来向她的儿子她的长子做最后道别)。
晚上十二点多时,一阵电话铃声紧急地响起,带着某种不祥,我的心一阵紧促,清源那头传来二弟的声音,母亲昏迷,已经住院,速来。
我马上想起春季时大个子男人撒尿的事,正验证了我一年中的不祥预感,我的脑海浮现如何抢救母亲讨回风水的预案,是拿把菜刀拿片红布去西院西北处做一番什么风俗操作,还是祭祀动作……最终还是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妻子红莉和我决定,先去清源县医院陪侍,然后见机行事。
我马上联系在路上开饭店的夏四娃,这个过去就在我们对门的南邻,一个亦叔亦友的世家发小,他比我小一岁,辈份却要长我一辈,和我父亲同辈,在我日常的事务中常露身影的朋友,于是夏四娃开了车和我一同赶往清源。
母亲已经躺在县医院病床上,只是粗声地出着气,对于我的到来已经没有任何感觉,弟弟妹妹陪侍在旁,还有妹夫和弟媳(当时弟弟还没成家,已经订婚,结婚一切也已经顺遂,几个月后成亲,红事的被褥母亲已经做好了)。
母亲是紧急性脑出血。我无比的懊悔,后悔为什么出来时没有进行我那套不可告人的行动。上厕所时碰见我的父亲,这个铁一般刚强的男人,脸上有刚刚拭过泪水的痕迹,以他处世的聪明,大概率已经知道他即将失去这位陪伴多半生的伴侣,这个无与伦比的战友,这个能令他挚爱一生的女性。
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也许这注定就是母亲的宿命。我们一家人失措地过滤着时间的流失,否定着刚刚还坚定的信念,一条又一条,什么转院,到太原继续治疗……在太原做军医的大姑有建议,可她同时又是比谁都清楚。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一点多,母亲几次呕血后去世。
母亲的白事如斯进行,在家放五天,于五天后出殡,一切顺利,正如她的人生,默默地来,默默地走,默默无闻,难让人察觉,不给人添麻烦。
她的亲人、家人、亲戚、邻居、朋友,都来送她最后一程,也许是她这一生最为风光的时刻。
唉!在以后的日子,我经常在无人的地方流泪,出门在外感觉脊背发凉,我以为世人都已经知道我是无妈的孩子。我一直以为娘娘是我人生最亲近的人,不想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是这样的大。
父亲在母亲去世十七年后,于2024年的夏季离开了我们。与母亲不同的是,父亲在病床上躺了将近四个月,我们兄妹都在病床前修善尽孝,情感上好过一点。
母亲去世几个月后二弟成婚,我也在几年后把旧院子做了翻修,(其实对于民间一些说法,我们家是不过分迷信的,好在家庭里的好事,又是那位在天的父母不愿意看到的呢)。我们兄妹的另一半也都是正直善良正经过日子的人,诚如我们的母亲,诚如我们的家庭,这是看不到的上辈子修来的,也是可看到的这辈子传承的,是母亲愿意看到的,也是父亲愿意看到的。
也许这就是一个人活着的意义,也是一个家庭组合的意义。谈到意义,其实也没甚意义,就是作为一个生命的存在过程,一个家庭繁衍生息的履历吧!你要活得好好的,哪怕累点忙点,能照顾人的时候就照顾一下,为上辈为下辈,为前世为来生,努力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