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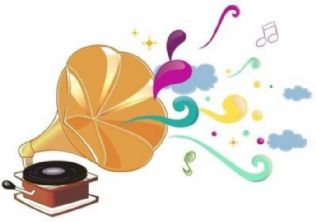

一个偶然机遇,记者接触到今年69岁的马峪乡桃园村人孙正千,闲聊中,他给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家的抗日故事。
我的外婆李玉成,1898年出生于汾州府城内李家巷,书香门第。8岁时生母得病身亡,留下11岁的姐姐,还有5岁的弟弟。父亲翌年娶继母到家,孰知继母吸毒瘾大,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很快败落。大姐才15岁便许于北武家巷生意人刘家,到我外婆15岁时大商户掌柜岳三魁为他侄儿提亲,当时我外公在汾阳念书,成亲后,办婚事要到清源羊圈峁,他的父亲提出不愿意,因此闹到公堂,两家争执不下,我外公的三叔遂买通衙门,公断不可退亲。
当时轿车就在衙门口停的,待车夫把我外婆抱放车上,家人即催马上路,直到清源都沟,已是午夜三四点。外婆在亲戚家休息片刻,改骑毛驴继续上路,这样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姑娘从来不接触牲畜,提心吊胆在崎岖的山路上颠颠簸簸,待到天明总算到达羊圈峁。在黑暗的旧社会,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抢亲,我外婆的父亲得病写来信,却不让知道,直至死了也不告知我外婆,在这举目无亲、暗无天日的难苦岁月中,外婆默默忍受着生活的不易与煎熬。
我外公热情好客、坦荡豪爽,江湖朋友很多。抗日战争期间,郭建领导的游击队伍经常活动在洛池渠、白石沟、后窑一带,完成任务后会回羊圈峁居住,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他们将之作为主要根据地之一。
自从有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朋友,外公家里常是宾朋满座。亲耳听闻日寇、汉奸在中华大地烧杀掳掠的种种暴行,也曾目睹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打日寇,外婆对这些离家背井、抗日为民、传播光明的子弟兵更施以毫无顾虑的接济保护,视兵如子,亲如鱼水,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也不让战士们受到丝毫损害,如郭建、赵连斌、张国俊、刘同山、薛培关等到了我外婆家就如同到了自己家一样,俨然就是自家人。
记得有一次孝义士兵刘同山病倒在我外婆家,不能归队,在我外婆的精心侍奉下身体逐渐康复,在他准备归队走后时间不长,忽然屋内的外婆听到刘同山在院中呼叫二姨,她预感不妙,随着答应了一声,顺着窗户缝隙看到刘同山身后有几个背枪的伪军,原来刘同山出了村不远就被出发的日本伪兵抓获,盘问他时,急中生智谎说是在羊圈峁看望他二姨李玉成,当一个军官模样的质问我外婆,“他是你外甥,”我外婆冷静而斩钉截铁地回答“是!”,你能保证他不是八路吗?我外婆也坚定地说“是!”,因为汾阳孝义语言相同,伪军官告诉我外婆:“他要是八路你应该清楚的知道后果。”
放走刘同山后不久,敌伪查清刘同山确实是八路,当即禁闭了我外婆,绑走了我十一二岁的舅舅岳元海,后经过抗日区长郭建,配合地下组织多方面的活动,出了五佰白洋才赎回了我舅岳元海。
解放以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但都念念不忘相互的恩情,经常书信往来,好几次郭建请我外婆到他家居住,到他的工作地省委作客,刘同山、薛培关也曾多次到羊圈峁看望我外婆。
1972年,这位坚强慈祥、流离失所的老人脑溢血倒在了南营留我二姨家,送回了奋斗难忘的羊圈峁,薄葬山峁,终年73岁。
看照片忆往事,这张照相是我家50年前的全家像,我记得为了给薛培关回封信,寄张全家照,特意到清源照相馆照的,说起薛培关,我们那里把腿短、体胖、个子矮的人比喻成薛培关。
我妈讲,那是在1945年初秋,天刚亮,赵连斌领的五六个战士到我家让快给他们做点饭吃,当时做了一锅汤饭和小米粥,战士们正狼吞虎咽地吃着,忽然有位邻居跑来报信,说日伪有十几个人已经进村了,急忙中战士们放下碗、迅速爬墙上房逃走,小个子薛培关急得几次都没有爬上墙去,这时我父母也急得在院中团团转,我妈说当时她怀里还抱着我,恍惚间,她看到了厨房顶上的席卷,急忙告诉我爸快把薛培关扶上厨顶,藏到卷席中。
刚刚藏好薛培关,进了家门,日伪已经闯开街门进院直奔我家,还没回过神来的父母,只得愣怔怔的站在那里,母亲心中扑通乱跳,对我的安危甚是担忧。看着乱七八糟的锅碗,残留的饭食时,其中一长官气势汹汹的质问,“你家干什么来?”我父母一时想不出其他理由,又怕引来对方怀疑,只可实话实说,“是接待八路吃饭,”又问八路去了哪里,我父机警的谎说是往西沟方向逃走,只想着敌人按他所说前去追寻,果不其然,敌人按父亲“指示”前去“追捕,”敌人顺河追了一阵,却不见踪影,才知父亲所言为虚,终怒不可遏得返回我家砸锅摔盆,就在他们施展其猖狂行径的时候,突然两面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伪恐遭到八路的包围,赶忙仓惶逃走,临逃时,那凶狠的日寇,还不忘向我父亲小腿部捅了一刀,赵连斌后来告诉我父说,他们临出村时,分成两组,一组上西坡,一组爬东山,当看到敌人返回村里时,怕我家遭到不测,先向村边射了几枪,然后绕到村前,准备抗击日伪。在那战乱恐怖的岁月里,我村桃园一带黑夜八路活动,白天敌伪骚扰,惊心动魄的事时常遭遇。
解放后,在我的记忆里,那些革命老前辈们经常和我家书来信往,尤其薛培关,为了他的性命安全,我父母几度冒着危险,不顾生死,双方经常通信抒情叙旧。他把自己的结婚照寄到我家,看到他女人比他还高出一头;有一张他家生了贵子的幸福全家相,邮到我家让我们两家同乐;最让我难忘的是,1961年最饿的时候,这位小个子老朋友去看我们,当等到我父从地里回来时,两位老熟的陌生人久久握住颤抖的双手,默默无语,泪流满面,当时已是交城县粮食局局长的薛培关只以为革命成功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没曾想三年自然灾害和公共食堂生活让许多人仍生活困顿,看到我爹浮肿的体态,还在生产队带兵劳作,顿觉心酸。记得当时我家连顿像样的饭食也不能招待朋友,久久无声似有声,最后流泪离别,临近傍晚,我妈从我的书包下发现了20斤全国粮票。
人到老年,总会有诸多往事齐齐涌上心头,而今借贵报一角,聊表敬意,谨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