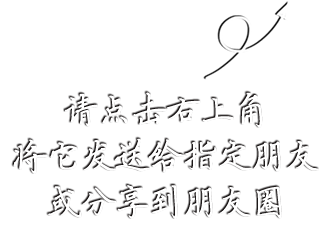刚走了大约一百五十米,就听得一个拿捏得娇声娇气的声音唱起来:
“叫大娘,
快坐下,
你闺女有两句知心话。
哎呀,我的大娘呀!(又有一个人拉着调儿说‘俺娃娃说吧’。)
七月里,
风光好,
提上篮篮去摘豆角。
哎呀,我的大娘呀!(摘豆角咋没把大娘叫上?)
俺家的豆角地,
离村好几里,
半路上碰上个俊后生。
哎呀,我的大娘呀!(哟,怎么没让我碰上?)那后生,笑嘻嘻,一把就把俺们拉进高粱地。哎呀,我的大娘呀!(俺娃娃快跑吧,还等甚的嘞?)地里都是草,奴的足足小,刚跑了几步就绊倒。哎呀,我的大娘呀!(俺娃娃快呜叫呀!)高粱长得高,奴的声音小,呜叫了几声也没人来到。哎呀,我的大娘呀!(哟,这可怎么办呀?)头朝东,脚朝西,
绿绸绸裤儿就褪到底。
哎呀,我的大娘呀!(哟,这可揽下戏了!)……”
越唱越难听,完全是对性的一种夸张的赤裸裸的描写,人们都嘻嘻哈哈地哄笑着。我身上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血液奔涌起来,一种躁动不安的羞涩使我有点晕晕乎乎,多么渴望见到小敔呵,哪怕仅仅与她说句话,激动迫切的心情,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呼吸越来越急促。一个声音高叫着,快走吧!不要再听下去了。
我不情愿地加快了脚步。“……”
歌声和笑声仍很响亮。
忽然,我发现灌木丛后面蹲着个人影,就轻轻地咳嗽一声,那人一回头,原来是村里的一个半大小伙子。我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那小伙子站起身,一边系裤带,一边红着脸说:“我和山娃子在下边浇地,怕跑了水,上来查看水道。”
山上的歌声和笑声虽不大,仍听得一清二楚。“……”我对那小伙子说:“地土干燥,容易跑水,你可多操点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