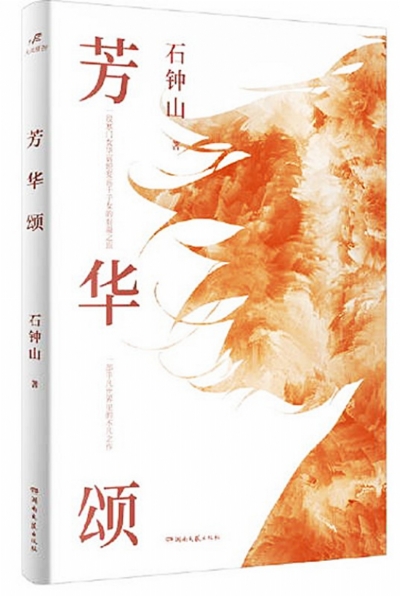
《芳华颂》,湖南文艺出版社。石钟山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一如既往选择的是军事题材,除少数地方有些许抗美援朝战争场面的回溯之外,其余背景就是和平时期,而且还是以改革开放后的大时代为主干,主要人物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时期的军人或与军人有关的人们。
石钟山的这部长篇小说新作其“作法”基本也是中规中矩的。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最突出的一点则是在开篇不久就设计了一个“误解”,并充分利用这一点来不断推动整部作品情节的发展。
在《芳华颂》中,“误解”犹如为作品系上了一个大扣,既然有了“扣”自然就免不了要“解”,于是整部作品也就是在“系扣”与“解扣”的搏弈过程中缓缓前行,直至走向终局。为了延缓这个“解扣”的过程,同时也是为了支撑起一部长篇应有的长度与饱满度,围绕着“系扣”与“解扣”这条主线,石钟山又刻意设计了作品主人公董红梅与其他人物间的几组“△”关系:一是她在马平阳和李来权之间犹疑的情感抉择;二是董红梅在马平阳和谢秘书之间的心理彷徨;三是她和段师长、胡叔叔的背景关系;四是董红梅与姐姐和突然“失踪”的母亲间的亲情关系。经过这样一番设计,《芳华颂》整体情节的丰富性及情感的饱满度也就有了施展的空间和必要的保障。
不妨从石钟山为《芳华颂》设计的那个大扣——“误解”开始解析。“误解”了什么?作品开篇不久就清晰地予以“广而告之”:一号主角儿董红梅的身份被误解。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那拨入伍的女性新兵各自都有一些特殊的“背景”,董红梅自然也就不能例外。于是,在如此不动声色、合符逻辑、漫不经心的叙事中,她的家庭出身很自然地被“误解”为高干,而且还是从事“保密”工作那一特殊群体中的干部,这样一来,更为本来就是的“误解”又平添了一层保护——旁人不便多加打听,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然而,如此精心的设计看上去周密合理,但又实在经不住推敲,在现实生活中明显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和不可能。董红梅是入伍当兵而非一般地就业,而我们的征兵必须经过政审等一整套完整严格的程序;如果硬要说这一环节还有勉强“蒙混过关”可能的话,那么,后来红梅经历的提干、调入北京重要部门工作等这些个环节无能如何就不可能被“误解”了。更何况董红梅明知别人误解了自己的身份竟然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顺势揣着明白装糊涂,同样也存有极大的不合理。由于这个“误解”实在不合理,《芳华颂》的整体叙事过程就时时为某种“风险”所笼罩,毕竟支撑起整部作品的地基随时都有可能瓦解崩塌,后面的故事也就根本无从继续推进下去。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石钟山为作品埋下的另一个“悬念”。
这些本来就是一个近乎常识性的问题,有长时间从军经历的石钟山不可能不知道;以如此有悖常识的节点作为自己作品的“大扣”更是无异于给自己挖了个“大坑”,这样一种风险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石钟山同样不可能不知道。明知不可为却偏要有意为之,他究竟要玩什么?我就是抱着这种好奇心读完了《芳华颂》,且看石钟山怎么“玩”下去?
然而,随着作品的终卷,石钟山还真没有让自己跌入“坑”中,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大扣”不合理的不存在。“坑”依在,只不过是随着《芳华颂》情节的推进,读者的情感注意力逐渐被一种强大的“感染力”所“蒙蔽”、所牵引,面对环环相扣的“洒向人间皆是善”,根本顾不上考虑“合理”与否的问题了。
《芳华颂》大幕拉开不久,读者便知道了这个董红梅出身在地处东北一个极度贫脊的乡野,其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只是个炊事员,战争结束后以伤残之躯回乡务农,不久便离开人间;其母在她三岁时又“神秘”地从人间蒸发;家中唯有一个12岁的姐姐拉扯着她成长。按正常逻辑,此后董红梅的人生境遇可想而知,然而打这之后,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好人、“福星”接踵而来,似乎在接力式地拽着她一步步地摆脱苦难、走向幸福、绽放芳华。先是其父的战友,同样回乡务农的胡叔找到了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的排长、现在已经是师长的段玉龙“走后门”让董红梅当上了兵;也恰是这位当时还不曾露面的段师长让大伙儿对红梅有了“高干子女”的误解。到了部队,真“高干子女”的女兵们纷纷去了机关,而惟有“伪高干”出身的红梅则只能被安排到了基层连队的炊事班养猪。在这以后又是一连串的好人纷纷出场:她的直接领导林连长、战友马平阳和李来权;被提为排长这个“干”后集中培训时的室友江雪以及她男友刘所长一家;到北京工作后,曾经的“恩人”段师长夫妇终于露面并成为她的干爹干妈;江雪试图撮合成为她男友的谢秘书,还有马平阳的父母……
能称之为好人者自然需要善举,无善举不好人。红梅自己首先就是一个好人,作为全连惟一的女兵,踏踏实实地做好养猪的本职工作,为自己赢得了提干的机会并得到战友马平阳和李来权的爱慕;已知她并非“高干子女”的室友江雪更是通过自己男友刘所长位居要职的父亲想方设法帮她由边陲进入首都重要部门工作,并为他介绍了前途无限的谢秘书,使红梅得以有机会近距离结识段师长夫妇并成为他们的干女儿。而惟一的姐姐为了她的成长,自己不惜下嫁给一位比自己年长许多且身有顽疾的男子,将她送走当兵后又毅然决然地一再拒绝她回乡及经济上的资助,终日辛劳最终导致自己肝坏死……而当红梅毅然决定用自己的肝脏为姐姐做肝移植时,她身边的这群好人纷纷献出爱心做出善举,最终姐妹平安,皆大欢喜。至于红梅姐妹俩失踪多年的妈妈也终于有了消息,原来她是当年出门为姐妹俩借粮时因饿晕而坠入了悬崖……
就这样,整个阅读进入后半程时,开始存有的对作品所谓真实性的怀疑于不知不觉中渐渐为感动感动再感动所替代,作品开局时系上的那个大扣一一被解开。这种转化从何而来?掩卷而思,原来石钟山是在用一种充满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构筑这部《芳华颂》。现实之不足,理想来补齐正是浪漫主义文学最大的特征,这样一来,所谓可信度与合理性之类有关生活真实性的问题都不再重要。以这样的视角再来观照《芳华颂》,这恰是文坛不多见的一部充盈着饱满浪漫主义情怀、激情扬善的佳作;而再放眼看,石钟山以住的创作中其实也不无这种浪漫的痕迹,只不过是没有这部《芳华颂》表现得如此突显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