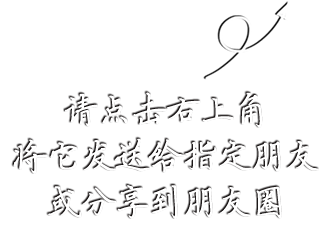我对所有会开花的植物都心怀敬畏。哪怕是一株蒲公英,一株米粒大小的苔花。在被绿色酱汁灌得满满当当的植物世界,一朵花她娇滴滴地缤纷着,纤弱细嫩的花瓣被一丛绿叶托举着,像舞台上的独舞者,徐徐张开裙裾,谁的眼睛不会为之拉开帘幕?
一朵花的诞生,会是怎样一个历经辛苦九死一生的过程?多少绿色的汁液才能熬炼出那一簇神秘的五彩斑斓?多少天仙的巧手才能将它们雕琢得那般样百态千姿?一株植物倾其所有,赴汤蹈火的悲壮全在那朵花里了。花开无言,但生命绽放的那一刻会让一株草在瞬间光芒四射,叶子们因为它们头顶的那一朵花而得以封官加爵——亲爱的,请看仔细些,我们可是花呦!
总以为会开花的花都是难养的。开花的过程,岂不就是要命的过程!我养过君子兰,养过杜鹃花,它们在开过一次花后,像一位可怜的产妇经历了大出血,不久后就死了。仙人掌也开花,但似乎它要老到成精才做开花的打算,而且花期很短,极惜命的做派。吊兰呢,也开花。我养过的金边吊兰,硕大一株植物,它开出的花比米粒还小,真是奸滑至极。
于是就有很多终其一生都不开花的植物。比如芦荟,比如绿萝,比如龙骨。我的屋里尽是这样的植物,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容易侍弄。这些花中的男子汉,比颜回还安贫乐道,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回不改其乐。它们连一箪食都不用,隔几日给它们一瓢饮就够了。
它们没有开花的使命,自然也不用经历那诸多的磨难艰辛,它们只管绿着,无忧无虑地绿着——你看或者不看,我都在这里不悲不喜。叶子一片又一片复制着,个头一点又一点抻拉着,它们绿得磅礴,绿得广阔,绿得浩浩荡荡,绿得千古不朽。我见过一个朋友家的绿萝,小小的一个花盆里长出了天大地大的的藤蔓和叶子,它们爬满了阳台的整面墙,造出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大有遮天蔽日气吞山河的架势。我不免担心照这样下去,是否会有一天那个家会变成绿萝的家,人呢,只会沦为那绿色王国里的几只小小寄生虫。
我不会养花,养出的绿色也是瘦骨嶙峋的。只给一瓢饮的植物,能活着就不简单了。植物的聪明远在人的想象之外。再说我的金边吊兰,一开始它入住我的阳台时,一挂一挂地往下吊,我嫌它杂乱无章,疯得过分,就把那些吊子都剪了。我还等着它重新再吊,像人的头发一样,长长一点修一修,整整齐齐,精精干干的。谁知,它再也不吊了。就那一丛叶子,长一圈,朽一圈。多狡猾啊,它怕再挨人的剪刀。
很多年,只养着些绿,不敢触碰花。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不爱花的。刚刚开始玩微信时,要给自己取个昵称,我毫不犹豫取了“叶子”,它像是蛰伏在我心里很久的一个名字,呼之欲出。我就是绿油油的一片叶子,生机盎然的,司空见惯的,素面朝天的,人云亦云的。
这点酸葡萄心理简直讳莫如深,直到鼓起勇气把一盆唤作“长寿花”的花捧回了家。
这盆花是老妈送给我的,她在养花这件事上比我有天分,住进楼房后,家里一年四季姹紫嫣红的。原本我是不愿意领它回家的,我怕这“薄命红颜”在我手上活不坚牢。可是听它这名字,再看看老妈屋里它团团簇簇的拥挤模样,我还是决定一试。
我挑了一盆最不起眼的,老妈说如果我不要,就要扔了的一盆,端回了家。它纤细单薄的一根杆,到肩部兀自长出一丛叶子,叶子中间又高高冒出了一支花,三朵,红艳艳的。像踩着高跷的舞者,颤颤悠悠,摇摇欲坠的。
就这么几朵小花,也让我羡慕。我想倘若人变成植物,我自己的头顶都不一定能开出这么几朵花来。
有绿不看绿,有花只看花。是我的眼睛太挑剔,太寂寞了罢,因为那几指甲盖的红,我觉得我的屋里完全是春机盎然,春色满园,一派春色。长寿花的叶片类似多肉,又似比多肉肥厚,多肉类的植物,想来是不难养的。
一株会开花还好养的植物,真是世间难得,而且绝不同于蒲公英,绝不是野花的类属。我知道,那血一样鲜艳的红色,也集聚了它身体里的精华,花开不易无可厚非,长寿花岂能免俗。只是啊,它身上的那股子顽皮劲,实在让人钦佩。要不,世界上那么多花,为何只有它被叫做“长寿花”呢。
一场花事一场劫。反言之,一场劫之为一场花事。真真是看似相同罢了。
在这株长寿花面前,我这片叶子唯有惭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