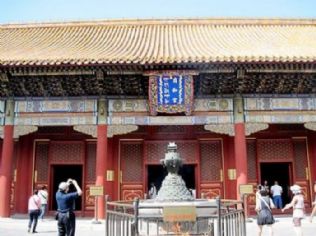


昨天送孩子们进京。
北京欢迎我们。前两天还是近四十度的高温,这两天却是夏天里少有的凉爽宜人。
学习的学校在昌平。比较远,出了五环还有40多公里。进校的时候,门卫说:“孩子们进去了就不让出了,进去吗?”听了心里真不舒服。原来还说下午带他们去想去的地方玩呢。问孩子们:“咱进吗?”他们说:“进吧。”此行目的明确,不容犹疑,所以进去了。
报道的程序类如我们学校。我心里告诉自己:等到上大学就是这样。心里一万个感慨,一千种滋味,一百个不舍。办好一切手续,报了到,到了宿舍,整理好床铺用品。叮咛再叮咛。
说好送过他们来,我就跟弟妹一起回家的。大家要走的时候,我忽然不想回了。于是让弟妹他们回家,我就近找了一个宾馆住下来,距离不足二百米,心里很安慰,觉得还跟在家里一样。
下午,出去转了昌平县城。这个地方僻远,但很朴素,还有一些人文情怀。当年北岛写《波动》,就想躲那儿;诗人海子生前工作生活也在这儿。
在街上我问一个少年附近有没有书店,他不仅很详细地比划书店的地点,而且还指点去哪购物,然后建议我可以坐三轮车过去。谢过他,我打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脚踏的,但也很有一百年前旧时代的味儿,很特别的感觉。
书店逛了一圈出来,专门找了一个小巷子钻进去。巷子不是胡同,不是静默的路和幽深的门,是一个接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店铺。粮油店,烧鸡店,饼铺,小吃店,房介所,婚介所……有一家杂货店,门大开,里面没人,木板门上两行字:
有事打电话:13XXXXXXXXX
这里,每一家都是开门敞户。有一家,一个女人在晃着婴儿车里的宝宝;有一家,摆一张方桌子,一个穿背心的男人,一脚踩在凳子上,一手在倒啤酒喝;有一家,夫妇俩在门口玩扑克,刚打完一把,在整牌,旁边有五六岁的女儿看,对父母的出牌作点评……
沿街所有的房子都伸出宽宽的檐,檐下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地上平铺着灰色的砖,比一般的略小一些,带着古老的亲切。
因为不熟,不敢探路,所以只能原路返回。我回来的时候,路的两边坐满了纳凉聊天的老人,他们每人手里都摇着一把裹了边的圆蒲扇。
大概别的地方,也会有相似的风景,司空见惯;但是因为是在这块土地,我就觉得别具一格。那就是让人回味无穷的京韵吧,尽管这不过街头短暂的一瞥。
每在这个时候,我都特别感谢上天对我的眷顾。
二
想到孩子们课余时间充足,怕没什么事做,上午去书店买了好多书。
中午退了宾馆的房,去看他们。最担心的是全英文上课,不适应,听不懂。见了面,还好。
昨天说食堂一楼的饭不合口味,我上二楼看了,比下边要好。所以说:“以后上二楼吃,别省着。”他们早不耐烦了,相视一笑,理都不待理我。我也就识趣地回家算了。
出来找车站,找车。问了一个小女孩,正好她也进城,我就跟着她一起走。结果还是在换乘车时走丢了。路上问了司机,在合适的地方下车,再换乘车。找站牌很容易,一下子就看到了。我以为十拿九稳了,就牢牢站这儿等。等了有快二十分钟,不见有车来。期间有三个人过来问路,我都摆手说:“别问我,我外地人。”
终于等的车来了。车门一开,司机师傅就探头说:“往东走,前面上车。”哪是东?这面吗?我问下车的人。人说是,你往前,始发站在前面。
我还没走几步,车上人很快下完了,“呼”一声从身边开走了。我真是气愤,为什么非得前面才能上?这不一样吗?错过了这趟不知还得等多久,所以气愤化作了动力,跑了几步,还好赶上了,只是走道里已站满了人。
我穿了尖的高跟鞋,站了那么久,跑了快一站路,又得站一路,而且分明是等了好久,真是懊恼沮丧。
不过我很快想明白了,在一个车站等那么久,身边居然没有一个人,而自己居然没有想到不对劲,怨谁?
当一个车站只有你一个人在等,一条路上只有你一个人在走的时候,你要小心。
那样,恐怕是你错了。
三
昨天中午,吃了一种做工很精致的烧饼。长方形,夹了馅,外面金黄,常说的外焦里嫩的那种。晚上,想吃面,找了一碗西红柿面吃。今早,喝了一杯豆浆,吃了两个小笼包。中午,吃了一点馄饨。要不是回到家里,吃了自家熬的米汤,烧的茄子,就不知道该吃什么好了。在外面吃饭,太发愁了,尤其是一个人,一口饭。所以特别怀念家里的粗茶淡饭。
但是,饭虽不合口,却可以充分感受精明的经营者与人的那种尊重。顾客是上帝,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
烧饼店的小老板,很年轻,衣着和店面都非常干净,而且很客气,一直站在门边微笑着迎接顾客。店里的顾客,不管一群人还是一个人,服务员都会按着次序用盘子端来你点的饭菜;然后很客气的送来餐巾纸;即便找出的是五毛零钱,他们也会双手送上;即便你不过消费两块钱,出门的时候,他们会说:“请慢走,欢迎再来!”我想如果人的心理大多一样的话,进店的人都应该是冲这一点来的。
宾馆的服务员,都会微笑着和你打个招呼。提出一个什么要求,她们会想办法满足你。我指出了房间里的一点不合适,那个年轻的小姑娘笑着说:“你真细心。”
在我们这个地方,可恶的事情太多。理发店的店员,会根据你消费的多少,给你不同的待遇。烫染很能赚钱,他就围着你转;剪个短发,如果人够多,对不起,只能晾你一边。就在我们出发进火车站的时候,我还见到一对外地夫妇,被一个卖桃子的小贩强扯着不放,旁边有人怀着恶意打圆场:“你就十五块钱买了吧。”我没工夫看他到底买得到多少桃子,只是忽然想到,三个多小时后我自己就也是外地人了。但是,在这里,你时刻感受到的是它无限的包容,没有异地他乡的寂寞和窘迫。
一个城市,一个地方,该有它独特的魅力。
从容自律,雍容高贵,这是我们的首都最基本的素质。
四
京城蕴含无限,可看的东西太多。但我最牵挂的却是地坛。
今天我说准备去地坛,人们都很奇怪:地坛有什么好看的?要去应该去天坛吧?天地日月,就数那儿没意思。
但我固执己见。
一路上问了许多人,就是本地人,有的根本不知道,有的有一点影儿。有一点影儿的,有的说在鼓楼一带吧,有的说在雍和宫吧。我在地铁车站看看柱子上的站台指示表,还好,两地在一个方向,没离谱,就上了车。
因为已经买好了回家的车票,得先确定一下车站的位置,判断距离,计算好时间。地铁里,座位旁边坐了两女学生,听说话的内容是本地人。我问她们车站的大致方向,她们居然不知道,很不好意思。我笑着说:“这地儿太大了。”近前站着的一位先生说:“要去车站的话,好像不是这个方向。”我说:“我是先去地坛看看,然后再去车站,想知道一下大致方位,好安排时间。”两女学生急着说:“地坛我们知道,我们就去雍和宫那儿,可以给你指路。”我说:“那再好没有了,谢谢啊!”但她俩相视一笑,问我说:“你去地坛看什么呢?那里好像也没什么可看的。”我说:“也就是看一下,有个心愿,一种特殊的感情吧。”
地面上坐公交,转了一辆又一辆;然后钻到地下乘地铁,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坐的早晕头转向了。路生疏,总得问人,问的自己都烦了。有人带路,真的再好没有。
年轻的时候,我方向感特好,是值得自豪的事。记得十年前在这儿,傍晚时分乘地铁到王府井,那时候还是人工售票的。一从地下回到地上,我就能判断东南西北。
岁月无情,风干了水分,剥蚀了鲜活,瓦解了斗志,摧毁了记忆。
五
雍和宫出了地铁,远远的,已可以看到地坛的南门。这几天,找一个什么地方太难了,这倒是很在意料之外。
我钟情这个地方,是因为一篇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我想知道,怎样一个园,可以将完全陷入泥淖的一双腿拔出,让一个残缺肢体的灵魂更健全地飞扬。
印象中,是一个凌乱残破荒凉的园子。我的心情正渴望一种荒芜的衬托。
但是,我是多么失望啊!
地坛,太整齐,太茂盛,太新。
长方形砖铺成的路,棱角分明,将一个园子切割得齐齐整整;路上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也没有。新安置的长椅,藏在被路切割成一块一块的茂密的林子里,两颗粗壮的树之间。很少有行人坐着,它们都静静得呆在那儿,散发着新木的光泽。
树很多。进来之后,几乎就看不到天了。沿路有合抱的古树,老态得很;桧柏栽的整齐,长得也争气,一律一个模样,像个巨大的锥子蹲在那里,有五层楼那么高。侧柏要稀疏些,看得到它们粗的细的但无一列外侧向一边的树干。我猜想“侧柏”的名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银杏树高大,叶子却小巧,像千千万万个小小扇子聚在一块儿。我见许多人拿一片夹在书里做标本,确实精致。这些树有人领养,树上挂着小牌子,写着树名,科属,领养人,给了这些植物人间温馨的气息。美的还是松树。我自己觉得无论在那里,松树都是独占鳌头的。它不像别的树,一种就一个形,一眼看个穿。它会让人留恋回首,因为姿态万千。那些平展展的树冠,我说不出来它们怎么弯,怎么绕,反正是无论怎样长着,形状疏密都是刚刚好,富于意境。如果说别的树平凡,松树则是极具艺术气质的。
园中已有一个简单的游乐场。正在建一个中医养生游艺园,与别处一般的亭台楼阁,游廊曲水。盆栽的荷花,金属或木雕,小小的观赏桥,各种造型的垃圾桶……还没有完工,空气里有浓重的油漆味。
出了这个园子,一位先生迎面而来,听到他自言自语:“这个园子,已经没有什么古的东西了。”
正是我想说的。
远远的围墙,虽然墙头鲜亮,墙身却是朦胧的灰,有一丝古意。我近前看,确实如此。砌墙的砖,跟铺地的差不多大,有我三掌长,宽也有近一掌。墙体下面宽上面窄一些,结实的很。
离开大路,我特意进了一条窄窄的林中路。没有人,但鸟声不断。我想,当年二十岁失去了双腿的史铁生,该是在这里思索他的人生,进而开始生命的探讨的吧,那时的地坛是那么契合他的心境。不过无论荒芜还是生机,外在的自然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心灵的彻悟和解放。我倒是常关注他的消息,包括他的作品,他的活动,他的朋友,他的病。也不知道今天他还常来否?
一个多小时后,我离开地坛。
又一个多小时后,我坐在动车上。车缓缓地驶离京城,将几天不辨东西的奔波统统丢在身后,将一个心愿和这些日子里纷繁复杂的思绪统统丢在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