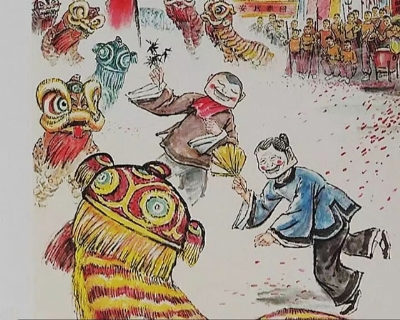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聊起吃饭的事,忽然就想起小时候有一年夏天,我们去邻村我老大姨家。谁带着我我不记得了,老大姨是我奶奶的大姐,我应该是跟着奶奶去的。记得清楚的是中午吃饭,不像今天这样在屋子里摆大桌子,杯盘碗碟,大家团座,而是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大门道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老大姨的媳妇,也就是我的婶婶,做好一大家人的饭,她最后过来吃,大约是热得厉害,她脱去了衬衫,这样上身就再没有遮拦了。一门道人,我们谁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就是非常自然。街上有一个人经过,他笑着对婶婶说:“那是干啥呢?”婶婶眼都不抬,一边挑着几根面条往嘴里送,一边爽快地说:“卖肉哩!”
这件事又让我想起另一件事。
我家的老房子在村子西南,不管是去村东上幼儿园,还是后来去村北上小学,都要经过贯通村子南北的那条大街。临街有一户人家,老人老实木讷,儿子木讷老实,路过他家低矮的土墙和低矮的街门的时候,感觉那墙和门都是愚拙的,就是今天想起来,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还是那种感觉。有一年春节,过那个街门,我看到门上的对联,右面是:饺子油糕片儿汤,左面是:新鞋新帽新衣裳,横批是:幸福人家。
四五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吃过多少次饭,也不知道见过多少对联,唯有那次吃饭和那家的对联,在记忆里扎了根。
今天偶然看到陆游《游山西村》里“衣冠简朴古风存”,忽然想起又一件事。一年国庆节去北武当,下山的时候路过一个农家,门口摆着一个铁桶,一个脸盆,脸盆里滚着三五个梨,桶里还有半桶。每次去这些地方,碰到当地村民卖一点自家的出产,不管什么总要买点。我们停车去买梨,称好了,18块钱,我给了20,说不用找了。这下好了,那位卖梨的老乡,在桶里剩下的梨里乱翻,找出一个来,说:“这个也好,给你!”再翻,再找出一个来递给我,然后还不肯停歇,还翻。大概是觉得找不出顺眼的了,他指着院子里的梨树说:“树上有,你们去树上摘去!”我们就进去参观了一下院子,从树上摘了一个梨,那老乡还说:“摘吧,摘吧,自己长的!”看那架式,就是这不用找的两块钱,可以随便摘。
忽然就有了醍醐灌顶的意思——所谓民风民俗,其实就是习惯,习惯了淳朴就淳朴,习惯了厚道就厚道,习惯了简单就简单,习惯了知足就知足——然而这习惯,既来自于脚下的土壤,也形成土壤。
我出生的地方北依潇河,沿岸曾经是我们这一带最肥沃的土地,每到春季,旋犁过的土地沟那么深,土那么厚,一脚踩下去腿就拔不出来,种什么产什么,都没有歇地那一说。我问为什么,乡人们说,那自然,潇河水每浇一次,就会留下一层泥沙,新鲜,养分足,那是最好的土。
我们西面,有著名的迎南风葡萄,除了地脉,还因为位于山南,温度适宜,光照充足。
我们南面,有最好的地瓜,因为土质沙,地瓜外形匀称,口感干,面,甜。
葡萄和地瓜特别甜,玉米特别香,谷子、豆子特别饱满,人也特别简单、知足——他们相信潇河水和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底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方水土,都会形成它的地域情调——过去叫“风俗”,现在叫“文化”。每一个个体,都是它庞大结构里细微的一支。一个人,只要他生长在一片干净的土地上,他就心地真纯,那么,在他眼里,一切就都是干净美好的,哪怕是裸体或者是饺子油糕片儿汤,都不带有一点邪恶和庸俗。
所以,只要我想起我那位婶婶,想起贴着那副对联的人家,还有那些非常淳朴的山民,总是觉得特别美好。其实,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不是某件事某个人,而是那种因单纯、知足而让人很熨帖的淳朴的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