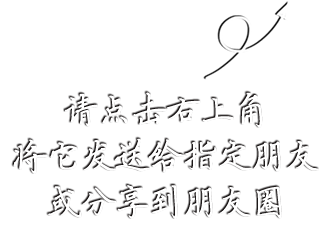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一些老同志受到了牵连,被打倒、靠边站,受到了不应有的“待遇”。1968年7月,为了把他们“解放”出来,与人民站在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对他们要重新认真的审查甄别。我部驻地张家口地区革委会成立了“审干组”,并请各驻军单位选派“根子正、思想红”的同志参加,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因时间紧,当吉普车送我到革委会时,已有五六个同志报到了。我们八九个军人,住在一幢废弃小楼的会议室内。会议室三面是落地玻璃大窗,一面是通向走廊的推拉门,据说是日军占据时修建的。
学习几天文件后,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与原地委某处的一位领导,负责对地区“农村口”十几个县的靠边站的县处级干部进行审查。这位处领导姓韩,我们都称他为韩主任,是“三八”式老干部。他告诉我,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老同志,要看大节,不要抓住小问题不放,要深入作调查研究,不走马观花,要认真分析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与韩主任一道工作,使我受益匪浅。我们小组在人事档案室办公,查阅、摘抄有关资料十分方便。档案员小齐,三十出头,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是人事处的干事,写的一笔好字,文章写得又好,曾借调当了专区领导的秘书。“运动”开始后又回到人事处管了档案。她性格开朗直爽,热情豪放,乐于助人,常帮助阅卷人抄录档案资料。
时间过得很快。国庆节前,我们小组已对三个县的原领导干部进行了审查,并对原“造反派”做出的打倒理由,有理有据地加以重新认定,提出处理意见。当举国欢度国庆节时,我却得了不该得的小病住进了251医院。打针消炎,动刀切除,折腾了十几天。这天上午出院了,回到那个小楼,人去楼空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床板上、地面上覆盖着一层灰尘,几张破碎的纸片在地面飘零。他们都搬家了,我的行李到哪里去了?在档案室,小齐笑嘻嘻地迎了上来。她告诉我,天气很快要变冷了,机关后勤部的同志,要把住在旧楼会议室的八九位军人,安排在比较暖和的室内过冬。他们把你安排在我曾经用过的那间小办公室内,你的铺盖他们搬过来了。后勤部如此关心我们几位军人的生活,让我很高兴。
她的那间小办公室,已经清扫得干干净净了。门窗玻璃上挡光的纸清洗了,办公桌、文件柜、地面都擦拭得一干二净,单人床上铺着一条白底蓝条纹的、印着“公用”两个红色大字的床单,显得很雅净。她告诉我,床单才洗过,被子放在文件柜内,都不脏,天气冷了,可以放心使用。她做得很到位,我始料不及,令我敬佩。
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柳絮纷飞,蜂蝶飞舞,蚊蝇也在脏乱处滋生。一天夜里,身上奇痒,还起了一些扁平疙瘩,好象是过敏的荨麻疹。几天后,我终于发现是臭虫作怪。这事让审干组的同志们知道了,大家都在议论,为消灭臭虫献计献策。这天是周六,起床后,我将床垫和两套褥被都晾晒到后院树上拴好的背包绳上,为灭臭虫做准备。午饭后,四五位同志提着暖瓶来了,小齐是当地人,她能找到卖农药的地方,她买来了“六六六”和“滴滴涕”。杀灭臭虫的战斗打响了!先给抬出室外的单人床,洗开水澡,五六把暖壶,轮番浇灌,别说小小的臭虫,就是浇在猪身上,也能脱了它的毛。室内的同志在搬桌抬柜,进行大扫除。桌柜怕湿的地方撒了六六六粉,外面及四周的墙壁上,喷洒了滴滴涕。灭臭虫的战斗很快结束了。同志们放弃午休,不怕脏累,为我除害,我非常感激。旁晚,我随部队的班车回军营了。
为赶班车,把被褥晾晒在外的事忘了。次日,坐了近一小时的公交车,于11点多赶回了地区机关。床还在那里躺着。到后院一看,不见褥被的踪影。是哪位好心人为我收起,还是……室内,床垫和公用褥被在桌上放着,上面一张稿纸上写着:先用这床褥被吧!字条是小齐写的,短短一语,告诉我,褥被没有丢,但把它们放到哪里呢?哦!我想明白了,原来是……我一个人在屋里吃力地挪动、摆弄着桌柜,给床铺入室打开通道。到室外,正试图挪床时,过来一位同志,他对我说:“解放军同志,我帮你抬吧!”在这位素不相识同志的帮助下,把床及桌柜都摆放到位。我非常感谢现实生活中的好同志。
室内药味很浓,我打开门窗,顺手拿了还未看完的《欧阳海之歌》,去了常青公园,公园内一片花红柳绿,处处欢歌笑语,一派欢乐景象。我却无心观赏,坐在河边的沙滩上,细品着英雄的事迹。
直到晚八点,小齐还未将我的褥被送回来,我只好用那套公用褥被了。星期一清晨,我依然起得很早,散步到公园门口,买了几个酥油饼,回到机关的那个小屋,准备用餐时,小齐推着自行车,载着我那已褪色的军绿被褥来了。还未来得及致谢,她却说:“没得到你的同意,就给你把被褥拆洗了。早几年我去部队探亲,经常同部队的家属,给战士们拆洗衣被,缝补衣袜,从来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抱起衣服就走,有时他们阻拦,还跟我们抢,但没有一个小伙子抢过我们这些女人们——其实他们是不好意思。战士们训练场上生龙活虎,打起仗来不怕牺牲,但是,在这个方面,却都是女同志们的手下败将。”她连珠炮式的一番话,让我忍俊不禁,她也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她原来还是位好军嫂!我正思忖着,她又开口了:“你的被子不算脏,但缝的针足有大有小,有窄有宽,弯弯曲曲,一看就不是你爱人做的,我说的对吧?”她算猜对了。当兵时,每位新战士都会领到一个针线包。小小针线包,大小不一,颜色各异,上面还绣着“向解放军学习,或当兵光荣、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里面装着的不仅是几根针,几小绺黑白红绿线,还装着地方乡亲们对子弟兵无限的爱和火热的情!我曾经用满载深情厚意的针线缝衣补袜,还能缝褥引被,我的针工不亚于一般女同志的技术。而这床被子正好是一位热情的新同志帮我做的。我却撒谎,不加争辩地说:“是我缝的,让你见笑了。”我叠着松软的带着肥皂芬芳气息的被子,感慨地说:“让你劳累了,十分感谢你这位军嫂!”并忘记男女有别、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谁知她也毫无顾忌地拉住了我的手,使我无法将手收回。我急忙说:“对不起,我失礼啦!”她可能看到我发热的颜面,不紧不慢地说:“你这位堂堂的军官,和女同志握手还害臊哩!”说真的,常年在军营过着半封闭式的生活,很少与地方同志打交道,与女同志交往就更少了。“你上班这么早,还没有吃早饭吧?”为了走出尴尬的困境,我把话题转移了。“我刚从公园门口买了酥油饼,我喜欢这种饼,就多买了几个,一块吃吧……”没等我把话说完,她抢着开口了:“做这种饼子,是我的拿手好戏,有机会我请你吃亲手烙的酥油饼。”我不假思索地说了声:“谢谢你!”谁知随意的一句应酬话,却又引来了麻烦。
塞外的气温昼夜温差大。虽近八月,白天依然很热。一天,晚饭后我开着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室外纳凉,见小齐与一青年走到我面前,我正要开口说话,小齐抢先发言了:“赵参谋,这是我爱人李斌。叫他李同志好了。”她爱人爽快地说:“赵参谋,小齐早给我说过,你为人真好。后来我知道,你正是报纸上找的那位办好事不留名的好人,让人十分敬佩。”我赶紧说:“遇到别人有危难,谁都会伸手相助,一点小事,何必挂齿。”李斌接着说:“我也当过兵,咱们也算战友吧。建军节就要到了,我俩请你‘八一’晚上到家里小聚,不知能否赏脸。”这可把我难住了。前几年,在地方搞“四清”时,部队明文规定:不准接受地方同志的礼物和宴请。现在,以军人身份参与地方工作,更应“慎独”才是。我以遵守纪律为由而谢绝。小齐这时也开口了:“给个面子吧!没别的意思,我们家小李也曾经是军人,在一起吃点家常便饭,谈谈部队生活。你不像东花园那个部队的刘干事爽快,他已同意来我家聚聚,你倒推辞起来了,真不够意思。”这俩口子既然把话说成这样,我只好答应了。
为了赴宴,建军节这天,我没有回部队,仍在档案室抄写有关资料,为考察下一名干部做着准备。中午下班时,小齐走到我面前小声说:“下午我请假了,一定来……”我还没有回话,她已离我而去。八一建军节是军人盛大隆重而又愉悦欢快的节日。这一天,除值勤分队及少数同志外,其他部门和人员都放假。地方党政领导还将组成慰问团,来军营登门拜访,征求意见,还送来戏剧或电影票,为部队官兵专场演出,或进行军民联欢。在生活物资困难时期,地方政府都要给部队特供一批紧缺副食品。在最困难的那两年,还真的象陕北乡亲们那样,给我们送来了整猪整羊,令官兵们感动不已。今年这个建军节,部队的情况将是如何呢?尽管不在现场,但热闹情景是可以想象到的。我去赴宴,绝非为了吃,可当作军民之间小型的联欢吧,这个理由是否可以说得过去?
午饭时,刘干事在食堂找到了我。他说:“咱们买点什么礼品,总不能空手去吧。”“去年在251医院的军人服务社买了两瓶沙城酒厂的干红葡萄酒,这个酒不错,还出口呢。你看行吗?”刘干事说:“行。那我买点什么?”他非要再送点礼物。“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买两件小玩具吧。她家有两个孩子。”刘干事采纳了我的意见。
华灯初放时,我与刘干事在去往小齐家的路上,不论大街还是小巷,随处可见贴在墙上的写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标语。我与刘干事一进大院,李斌师傅就迎了过来。两位男子,听到我们说话后,也从屋里走了出来。“这两位是我的朋友,都在汽车站开车”,李师傅介绍说,“这一位姓高,那一位姓王。”我俩与他们一一握手,小齐在门口把我们迎到室内。她家住房面积不大,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客厅。一张圆桌上摆放着一个果盘、茶具,还有一盒当地产的“大境门牌”香烟。闲聊片刻,小齐端上菜来,有荤有素。我欣赏柴沟堡(怀安县城)的名吃烤全兔,和一碟咸菜。在张家口一带,无论是家庭便宴,还是盛大的红白宴会,咸菜总是不可缺少的。本来是观察新媳妇或家庭主妇厨艺的一种小技,以后却都以购买的咸菜代替了。李师傅从厨柜里拿出了一瓶汾酒。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们运输团在山西晋中一带驻训,领导派他和几名战友去帮助汾阳杏花村汾酒厂运输原料。任务完成后,酒厂送他们每人两瓶酒。解放军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何况是这种稀缺的名酒呢!再三讲明军纪后,酒厂以出厂价收了款。我和刘干事都不能喝酒,在我俩再三主张之下,打开了葡萄酒。席间,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脑海里,我曾经坐过高师傅开的车,说:“想起来了,我坐过高师傅开的车。那天我与韩主任去霸上沽源,我晕车,你让我坐到副驾驶座位。车行到狼窝沟时,我还是经不住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结果,是你把车停好,让你的副手把那些又脏又臭的污物清洗了,让我很感动。”“我真要感谢你,”高师傅站起来说,“你还记的吧,过了狼窝沟,发动机‘开锅’了,路过一个小村,车停下后,我下车找水。忽然,车向下滑去,是你紧急拉了手闸,才避免了事故。你还记的吧,全车人为你鼓掌。今天在李师傅这里遇到您,真是太高兴了。”高师傅激动地与我握手又向我敬酒。推杯换盏,热闹的场面,却把东道主和她的两个孩子忽略了。李师傅告诉我们:把孩子们送到爷爷奶奶家了,怕他们捣乱。我们给买的玩具,他替他们收下了。我向门外的小齐说:“小齐,快进来再跟大家喝几杯。”小齐满脸不高兴地进了屋内说:“小高、小王都叫我嫂子,刘干事略大我一两个月,你比我小一岁,你应当叫我大姐才是。”“我不敢叫你大姐,不然,李师傅要‘吃醋’了。”我这样反驳道。李师傅也亮明他的观点:“她有两个姐姐,她爹妈望子心切,就给小齐取了这个名字。名字是个代号。当年,她在信中还不是哥呀兄呀的叫我。我绝不会成为她的弟吧!”“去你的!如不是你追的紧,说不定我还会有姐弟恋呢!”小齐的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不一会儿,小齐端上了一笼莜面窝窝和一盆羊肉口蘑汤,汤中红红的胡萝卜、白白的山药,黑黑的木耳十分养眼;汤上面漂着青青的香菜,黄黄的虾米皮,薄薄的油花,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色香味俱全,让人垂涎三尺,食欲大增。然而,因肚量有限,只品尝了一点。不大一会儿,小齐又端来了满满一盆绿豆稀饭和一盘酥油饼,我虽然好吃酥油饼,但一点也吃不动了。还是小齐想得周到,她已包了四份酥油饼,让我们带回去分享。
圆圆的饼满满的汤,这顿庆“八一”的军民联欢便宴,让我至今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