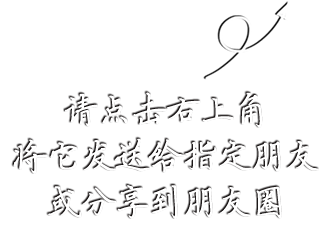33岁的今年,我的世界开始变得鸡飞狗跳起来,我甚至都掌控不了作为一家之主的方向,首先是我的父母不再训斥和辱骂我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渐渐进入日已偏西的状态,接着,我和堂客(媳妇)不再是同床异梦,而是异床异梦,再接着,我的儿女们也不再呼应我,幼稚的他们开始遵循自己的生活习惯,我行我素起来。
一种莫大的悲伤在我内心翻滚,终于有了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我想这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坎吧,有的人的坎在36岁上,而我的坎却是在33岁,比他们要提前三年。
三年?什么概念?我突然想起了晓晓(人名),因为上次见她就是在三年前,而上上次见她则是13年前,那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她呢,兴许再也见不着了。因为前几天,村子里就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说晓晓在南方的城市里发大财了,身价至少上千万,有房有车还有自己的工厂,把父母兄弟都接过去了,要真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她还回来干什么?
有的人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我们每一个心中可能都雪藏有这样一个人,他(她)是你情感世界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为她的存在,你才可以慢慢地熬着、苦苦地撑着,直到撑到英年早逝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晓晓走之前的一天,她使劲地挽着我的手,从镇上的中铺街走到新铺街,再从新铺街走到中铺街,她低着头,像是在寻找什么宝贝似的。最后,我拉着她去建国中学转了一圈,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着《渴望》,她听得如痴如醉了,还眼巴巴地问我“明天你还能陪我上街吗”?我信誓旦旦地说“没问题”,她笑了。但第二天,家里的老母猪就病了,一大早,父亲就要我去找兽医张汉元过来,我便把陪晓晓的事忘了个干干净净。
过了三天,我才明白过来,其实她的出走是有征兆的,还是在玉米地里锄草的时候,她就带着哭腔对我说“我们离开洪甘冲吧,你带我一起去外面吧,哪里都行,好吗?那样就没有人能够管我们了”。可我不知道她说的外面到底在哪里,在我的印象里,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十几里地的镇上了。
晓晓走了,我走在房前屋后、山间河边的时候,心像掏空一样,往前的一幕幕都那么触手可及:当我躺在河滩的草地上,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一根枯黄的狗尾巴草时,她只是躺在我的旁边,双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正月里舞龙的时候,我正准备和邻村的舞龙队伍大干一场,都已经准备好了鸟铳,就等着头人一声令下,就要对着人群开火了,娇小的晓晓不知从哪个地方钻了出来,居然把我手中的鸟铳夺了下来,硬是把我拖回了村子里,她气喘吁吁地数落着“你嫌你娘和我做的饭都不好吃!想去吃牢饭啊”?我的暴戾之气一下跑得无影无踪了,更明白了的是,晓晓是在关键时刻走的,河对面的聂姓人家马上就要到她家去提亲了,他父母和媒人都谈好了具体的礼金。而她买完那张离家的车票后,身上只剩下二十块钱。
晓晓走了,我的世界照旧,掏空感只是三五几个月的事情,我的身边马上就有了山背后另一个李姓女子,我好像跨过了那个坎,其实我永远都跨不过那个坎。我现在就开始眼鼓鼓地向村子里的一些年长者发难:同姓就真的不能结合吗,其它的地方难道也一样?这他妈的估计是洪甘冲的土规矩吧!他们要是再敢多说一句的话,我是真的准备动粗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多少个夜晚,我都是一个人泪光明亮地站在杂草丛生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