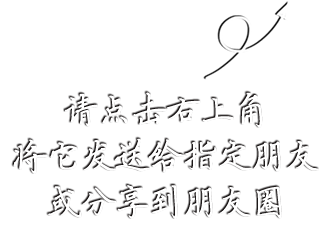记得那是2000年,单位第一次建高层住宅,恰好分配到我们这批人。住进这登高眺远的新楼房,晚上总是辗转反侧睡不着。妻子问我“怎么不习惯了?”我说,倒也不是不适应,3层到9层,有啥适不适应的。但每搬一次家,总情不自禁地想,父母亲那个年代的不易。母亲在百货公司站柜台,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照了一辈子半身像”;父亲先前是政府干部,后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了学校,当了一名被监督改造的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末了调回县文化系统工作,都是没有实力依托建房的单位。所以小时我家总是“串房檐”,父母每月几十块钱的微薄工资,县城里转着租住私人住宅。我们姊妹四个,每出生一个,就换一处住址。我在南营留谁家院儿里出生的,父母说过我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大妹妹出生在官道街板娃家院儿里;二妹妹生在二完小对门毛玉儿家院儿里;弟弟生在阁儿上赵玉明家西屋。直到大后来,母亲托关系找门道,才住上东湖岸边的公租房宿舍。那实际上也是低洼潮湿的小平房,在父母,也是高兴的不得了啦!
不难想象,住房是父母亲这辈子,难以名状的心结。改革开放后,母亲退休在商业街开了自己的“又一店”,才有能力购置了宏乐小区这套一层东西朝向的楼房。当我睡在这居高临下,光线充足的新楼里。我问妻子,“你说我能睡的安逸吗?”妻子默默的点了点头,却为我的心结操起了心。之后,无意间在与某单位任领导的乡兄闲聊时,说起想给父母改善一下住宅条件。没想到乡兄当即一口应允,将单位分给他的一套新房让给我。我和妻子喜出望外,连忙交钱办手续,召集朋友现场勘测,筹划设计装修。两位精通工程的朋友,全身心的扑在装修上,事无巨细,一趟接一趟的,陪我和妻子跑装饰市场选材料。妻子的原则是:第一质量;第二环保。两位朋友从选择装修队伍,到采购材料、亲自监理,直到工程验收,清扫干净交付使用,三个月完成。晾晒了半年多,妻子开始采购家用电器、家具沙发和床上用品、全套厨具等等,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耗在新房陈设上。针头线脑都安顿好后,我们又在新房体验了几天生活。感觉万事俱备,可以邀请父母入住了。说话间已到2002年临近国庆节了,父母毫不犹豫的,赶在节前,入住到这套150多平米的新房里。记得父亲给新房贴的门联是“楼高心静风来翰墨香;居高气爽光足鹤寿长。横批:颐养天年”。(摘自《野草晚吟》)母亲邀请在太航仪表厂工作的舅舅和妗子来家里聚餐,父亲邀请俩位姑姑和姑夫一同前来新家齐聚。那年的国庆至春节,无论父母们的老姊妹亲,还是我们兄弟姊妹们,都在这个新房里,陪父母度过一个其乐融融,欢乐祥和的节日。父亲还写了两首深有感触的律诗“《迁居太原》。(一)五楼初装白亮新,西南光照满屋金。新床新柜新家具,老俩浑似度新婚。(二)古人梦想孙悟空,如今我辈事成真。一想胞亲来相会,电传驱车聚省城。《居并随记》(一)卅十河东西,稀古梦亦真。三迁新楼住,落脚太原城。(二)楼林丛耸中,五楼是咱家。登高爬山累,进屋似天堂。(摘自《野草晚吟》)
正月过后,我们毕竟不能常陪在父母身边,兄弟姐妹陆续各自回家时,我看出父母嫌这里人生地不熟孤单了,另外,毕竟老胳膊老腿爬五楼不太方便。就这样住了三个多月,便又回清徐老家了。
谁曾想,这便是我们陪母亲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当年正月父母回家。十月母亲便病发,住进省心脑血管医院。不到半个月时间,连发三次病危通知,我托山大一院任副院长的思进同学找了专家,给母亲进行了会诊。原来母亲得的是扩心病。由风湿性关节炎,引发风湿性心脏病。几十年积劳成疾,已经无可挽回。怪不得母亲多年前就说,她每次体检比别人的心脏都大呢!可我们兄弟姐妹没人懂医,所以谁也没有引起重视。多年病灶导致心肌缺氧,心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停摆。我们通知舅舅和姨姨们尽快来探视。同时,安顿弟弟妹妹随时准备料理后事。当我电话通报弟弟时,他还责怪我胡说八道!也难怪,年轻的弟弟毕竟不太成熟。就连父亲也不一定了解母亲得的是啥病。舅舅妗子就近在太原,我接过来见了母亲最后一面,两位姨姨,也怀疑我的判断,觉得都在县城,早晚回来再见,就未能见上最后一面。10月20日午后,当我怀着忐忐忑忑的心境,将母亲送上弟弟接母亲回家汽车时,心想还能挺个十天八天的。未曾想,母亲竟倒在了家门口。
母亲,名李学英。但知道她真名的人很少,都喊她乳名“凤儿”,在县城繁华闹市的南门,百货一门市,多年站柜台直到退休。
她的音容笑貌,貌似长长的柜台,延伸进布票、棉花票、购物卷那个年代的千家万户。
记得临出院前一天,母亲病危成如此这般,还惦记着父亲的脚疾,她拉着我的手,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从她退休后开店的风风雨雨,到店面不得已交给弟弟弟媳经营,说到激动时泪语涟涟。她点评了家里老老少少所有的人,说了多年来从未说过的话。尽管起初母亲没把我当她最器重的儿子,而此刻却给我说了最贴心的话。每当我梦见与母亲泪目对视那一刻,便从梦中哭醒,妻子总是说:“又梦见了……。”
是的,母亲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