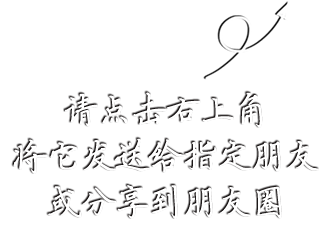还不到草长莺飞的日子,燕子先来了,它们在梁上衔泥筑巢。母亲指着燕子说又到春天了,这时候她就坐在门口的阳光里,手里是纳了一半的千层底,每一个结都被她拉得长长的,犹如对我们的爱丝丝缕缕,母亲的身影在墙上佝偻成沧桑的剪影。
年年一开春,母亲就开始纳鞋底做布鞋。小时候家里人多,她白天去地里劳作,晚上就趴在缝纫机上给我们做鞋帮。我们姐弟几个挤在缝纫机前指着碎花的鞋面挑拣,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母亲则透过缝纫机头下面的空隙看着我们温暖地笑。
许多年后的春天,母亲仍坐在那台老缝纫机前,趴在从窗户照进来金黄的光线里,戴着老花镜做着鞋帮。一群孩子挤在她身边喊着:姥姥,我要这双;奶奶,这双是我的。母亲从镜片上面看着几个孩子慈祥地笑。
母亲说,自己做的布鞋跟脚,穿着得劲儿,孩子们也嫌弃买的鞋捂脚,于是做鞋一直都是母亲一年中最大的工程。伏天里打上浆糊,把纯棉的布一层一层地粘在一起,晒干后按照鞋样儿做成鞋底。三伏天潮气大,她会早早地起来纺麻线,然后一针一线地纳鞋底。这么多年,母亲劳作的身影已经像一幅幅版画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近年来,集会上已经没有卖麻的了,母亲只能用棉线合成线绳纳鞋底。每每看到孩子们先从鞋底磨坏鞋子的时候,母亲都会叹气说,到底没有麻绳耐穿,不地道啊!
这两年,母亲的眼睛被诊断出白内障,我们姐弟就坚决不让她做布鞋了。我说现在哪还有穿布鞋的。母亲却说她穿不惯皮鞋,弟弟给母亲买来布鞋,母亲穿上走了几步摇了摇头。私下里我和妹妹说,我给咱妈做一双布鞋穿,妹妹吃惊地看着我。
作为长女,我多多少少还继承了点母亲的手艺。鞋底是以前母亲纳好的,我只负责做鞋帮,然后把鞋帮绱到鞋底上就成了。
坐在母亲经常坐的木凳上,心里隐隐有了一种责任感。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按着鞋样“刻鞋面”、“沿鞋口”、“绱松紧布”、“沿鞋边”,期间弄折了好几根缝纫机针。母亲在一旁感慨,这缝纫机要报废在你的手里喽。我说,没把手报废已经很幸运了。
绱鞋的时候我的手被针锥刺破,场面极其惨烈,一双鞋做好手臂已经酸疼得抬不起来了。母亲穿上我做的布鞋哑然失笑,不仅仅是难看,关键是松垮得只能趿拉着走,我很是泄气。妹妹们安慰我:姐,已经很不错了。母亲倒是很高兴,趿拉着来回地走,还说,当拖鞋也行。
细数了数,母亲每年做的布鞋不下几十双,这其中的辛苦我都无从体会。母亲说,脚是接地气的,必须舒服。多少年来,穿着母亲给予我们的爱走过了懵懂少年、豆蔻青春,现在人到中年才体会到了布鞋里装着的爱有多么深沉。
母亲揉着我的肩膀说,累坏了吧。母亲啊,我这才给您做了一双鞋,您为我们这些孩子做了一辈子的布鞋,您累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