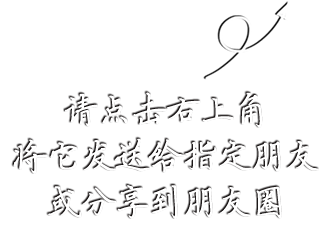时光荏苒,亲爱的姐姐离开我已经三年了。那是三年前的一个午夜,外甥自力来电话,告诉我姐姐不慎又摔跤了,正在昏迷。我赶快起床叫来女婿驾车,我们风驰电掣般地急行四十多公里,赶到姐姐身边。
卧室内一片寂静,姐姐的四个女儿和女婿,两个儿子和儿媳都默默地坐在床边,高高的输液瓶缓慢地向下滴着救命的液体。姐姐微微地闭着双眼,犹如在静静地睡觉。我身不由己地俯身到姐姐身边,嘴唇对着姐姐的耳畔轻轻地叫着:“姐姐!姐姐!我来了!”可亲爱的姐姐,失去了见到我时,常常挂在脸上的笑靥。我轻轻地推了推姐姐,竟然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种不祥之兆直刺我的心房,眼泪不由地滚落下来。姐姐的二儿媳告诉我,我的姐姐嘴里经常念念不忘地叫着我的名字,经常坐在窗户底下的板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院门,高兴地告诉他们:“你二舅舅快来看我了。”今天我来了,我的姐姐却一动不动,这让我心如刀绞。
姐姐长我13岁,从我呱呱坠地时,姐姐就对我呵护备至。我会吃饭了,姐姐总是将她碗里的,她认为最好的吃食送到我的嘴边。我会走路了,姐姐的背上总是驮着我这个顽皮的小弟。每当我顽劣不驯,母亲要责打时,姐姐总是赶快抱着我脱离现场,去到我可以“避难”的地方。我在县城读书时,离姐姐的家最近。每逢星期天,我总会去到姐姐的家里。她家并不富裕,可她总是竭尽全力给我做最香最甜的饭菜。我在太原读师范时,她将珍藏着的毛料给我做当时最为时髦的衣服,令同学们都羡慕我有这样的好姐姐。有一年,姐姐竟然托人将一筐家乡特产——沙金红杏,送到我工作的那个城市,让我的同事们也品尝到了甜美的果实。
姐姐是父母的长女,她以天生的孝心尽心竭力地孝敬着我们的父母。当她的身高还不及锅台时,姐姐就能替母亲剥葱剥蒜,至于摘菜洗碗这类的事,她是当仁不让地一直干到她出嫁为人妻。姐姐从十几岁开始,便经常参加田间劳动。据母亲说,每当劳动结束时,她都要主动地将母亲的工具,扛在肩头;有需要带回家的瓜果蔬菜,都是她一个人或扛或背,从来不让母亲承担。姐姐出嫁以后,她的家是盛产葡果的地方,每年瓜果成熟的季节,姐姐总是尽早地,将香甜的桃、杏、果子、葡萄送到母亲身边。在母亲患病的那几年,姐姐经常守在母亲身边,喂药、喂水,亲自做好饭菜,亲口尝试之后,送到母亲嘴里。她的行动,感动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姐姐对自己父母孝敬,对夫家的婆婆与兄弟姐妹也一视同仁。她的公公,流落在外,家中由叔叔当家。姐姐和她的婆婆便生活在这位叔叔的管束之下。这位叔叔十分吝啬相当刻薄,经常给自己的母亲,当然也包括我的姐姐,吃难以下咽的饭菜。她们婆媳挨饿成了家常便饭。我的姐姐,经常偷偷地在取暖的炕洞子里,利用烧炕的机会,烤熟一个胡萝卜或山药蛋,给婆婆吃。有时婆婆生病了,姐姐和侍候自己的母亲一样,为婆婆请医生,喂水喂药,直至病愈。当时,姐夫的弟弟和妹妹尚未成年,姐姐节衣缩食,尽量让幼小的弟弟妹妹吃饱吃好。当弟妹们到了结婚的年龄,姐姐和姐夫便竭尽所能,为弟妹提亲,准备衣、被以及日常用品等物,直至完婚成人,受到家人族人的一致称赞。
姐姐年轻时候家境困难,但她从来不叫苦喊累。她和姐夫一生克勤克俭,坚强地将他们的儿女抚养成人。随着国家的强盛,随着子女的成长,姐姐的生活也逐步得到了改善,晚年生活在子女孙辈的呵护之中,很是幸福。每当我去探望她时,她总是快乐地夸赞着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以及孙辈们对她的关爱。每当我去看望她时,她总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她说:“不管我的弟弟长到多大,永远都是我的小弟。”姐姐对我一生的关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