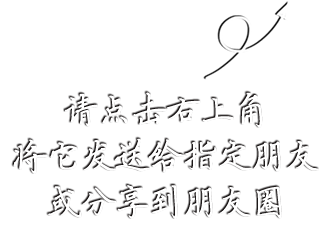我祖上清徐王答,却未曾回去住过一天。听母亲说1962年压缩户口,我是在集义乡西辽西村出生(1964)的。
母亲徐沟娘家是中农(外祖父能写会算,是个精明的小买卖人),17岁嫁到西辽西大户人家(富农,做布匹丝绸生意),丧偶后跟了在县里工作的同样丧偶成份为贫农的父亲,1955年至1961年间曾在县城安家。
在唯成份论年代,成份至关重要。每当需要填写时,究竟该填中农?富农?贫农?困扰了母亲一辈子。看得出她对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讳莫如深,很少提及也生怕他人知道。
4岁已模糊记得房子、院子、玩伴、邻居等,重要的是发生了一件铭心刻骨的大事,这件事占据几乎是4岁所能记忆部分的全部,也就此影响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一天晚上,一家人吃过饭刚刚睡下不久,突然院子里进来好多人,急促拍打我家房门,把全家人惊醒。
是母亲开的门,涌进来六七个,院子里好像还有。领头的拿着冲锋枪,说有人看到我父亲有枪,他们是奉命搜枪。父亲极力否认,母亲穿好衣服给他们翻箱倒柜搜找,连地上积放煤灰的盖板都一一打开来检查,其中一人还拿起我的玩具手枪仔细看了看,又放回盒子里。
这些人里间外间折腾约半个多时辰无枪可获,钱、粮票、东西什么也没拿,但提出要带父亲走,母亲死活不让,说等天亮你们再来再走。看到母亲与来人拉扯我害怕的嚎啕大哭起来,最后他们只好无奈地走了。
父亲连夜动身,骑车赶往县城。
第二天上午带来一辆大卡车,日用东西包括铺盖行李、箱柜桌椅、大缸小缸、盆盆罐罐……能带的都装上车,父亲随物品上了车斗,母亲抱着我与小姐姐三个人挤在轿子里。
我头一次见汽车、坐汽车,惊奇地注视着方向盘、档位杆……指针跳动的仪表盘靠我们这侧,分布大大小小黑色圆形按钮时不时被按下、拉起,其中一个一按就嘀嘀鸣响。
前路茫茫全然未知,我们情绪低落不敢说话。呆呆望向车窗外蓝天,淡淡白云几乎不动,紧盯住一朵好久直到汽车拐弯看不见再换盯一朵,太阳却忙着于云中钻进穿出,两旁树木、物体都长了翅膀齐刷刷飞向脑后。
坑坑洼洼一路颠簸,感觉走了好长好长在母亲怀里醒来,已抵达县城暂住到父亲的单位——手工业管理局。
后来知道,文革两大派系武斗,父亲属红总派,是兵团派的人抄的家。我曾亲眼看见开车拉我们的“三印儿伯伯”腰里别着手榴弹站岗。
再后来母亲说起走的当天,二姐躲在良隆二姨家,大姐在晋城,姐姐一家已在县城,大我两岁的大外甥也曾来村住过并一起玩耍。我家房子(全村最高门四合大院一里外间)600元卖给了本村一户贫农,而没有卖给她亡夫唯一的弟弟(院主),母亲也从此再未回去过。
《红楼梦》第一百五回皇上下令抄查了宁国府,黄一农院士考据到曹雪芹先父在任江宁织造期间也曾被革职抄家。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父亲文革初挨批斗被人活活打死了,留下五个孩子,他排行老四。
刚入高中时,我与班上西辽西同学说咱俩出生在一个村,他不信,回家问了母亲,我也问了母亲。得知他父亲恰恰在哪个时期,是队里会计,因账目被逼跳井身亡。
我常常想,那天晚上要不是母亲坚持,在哪个疯狂愚忠、人性扭曲的年代,父亲被来人带走会怎样?若没有发生抄家,我在西辽西种地,不也娶妻生子了吗?
这难道就是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