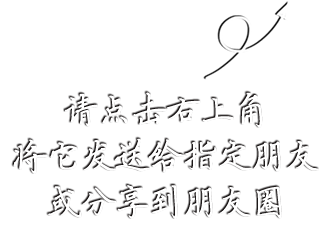我的父亲叫郝正科(1893年——1986年),母亲叫阎二变(1909年——1990年),已去世多年。每每回想起父亲流浪乞讨的苦难童年,回想起母亲生育抚养10个子女的艰辛岁月,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总是一齐涌上心头,常常令我潸然泪下。
我父亲的老家原在西谷村,爷爷年轻时,为谋生计在家中长辈的催促下,留下年轻的奶奶与刚出生不久的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家乡去东北沈阳谋生去了,一去数十年,杳无音讯。孤独、思念、苦闷、彷徨的奶奶原想以毒品麻醉神经消愁解闷,结果染上毒瘾,愁上加愁,把家里仅有的一点房屋田产变卖一空,最后一病不起,溘然长逝。11岁的父亲无所依靠,只好开始了沿街乞讨到处流浪,饥寒交迫的漂泊生活,后来听说徐沟城有慈善人家积善舍粥。便流浪到了徐沟城,白天吃点粥充饥,晚上便寄宿在武家庄阎恩德麦场敞棚里,在麦秸垛上挖个窟窿,钻进去过夜,心慈善良的阎恩德老俩口收留了我父亲,管吃饭,顺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放羊,喂牲口,扫院等杂活,还每年给些零花钱。
时光茬苒,父亲16岁时,已长得身强体壮,开始踏上了打工挣钱,实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之路。父亲把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的,那时武家庄熬盐户很多,父亲便承揽了朱蛮家三个盐池,早晨天不亮先清空盐池的泛泥,然后把新盐土倒进去,并按要求踩好。三个盐池需60多独轮车的盐土。早饭时间,父亲自己用烧柴土灶做一大锅稠小米粥或蒸一锅玉米面窝头,就点老咸菜。上午去村北嘉平渠挖河工清瘀泥。别人家不能干的,他全揽上,一上午一口气能挖三个河工。那时嘉平渠底宽堰高,河底沉淀的都是不利铁锹的胶泥,特别难干,每扔一锹,都要费很大劲,三个河工不出几身汗,根本干不完。午饭父亲就是早晨做得稠粥或窝头,加点水一热,喝上两碗。顾不上休息,父亲便又下地去了。晚饭后,父亲还要把早晨从三个盐池中清出的稀泥推到远处,常常一直干到深夜。
父亲做事勤恳有眼色,谁家有活都愿雇佣他,村里关狗儿家拉煤的牛车,每年冬天都愿雇我父亲赶车去西山拉煤。勤奋坚韧,朴实善良,这样的小伙子谁家能不喜欢呢,那时节,在吉科老人的关照下,父亲免费住进了他家宽敞的东房。
农闲时节,父亲却一刻也不敢轻闲,不是推着独轮车去拉煤,便是推着盐去太谷东山一带出售挣些零用钱。
十几年过去了,父亲凭着苦干实干,省吃俭用,日积月累,在村里逐渐置买了30亩地,自己盖了个简易的土坯房。在他33岁那年,与比他小16岁的母亲结婚成家。那时耕地自家没有黄牛,30亩地全是靠父亲用铁锹一锹锹铲出来,下种时,把三条腿的耧锯成一条腿,父亲前头拉,母亲后边摇,慢慢把30亩地种完。父亲惊人的吃苦能力,被村里人称为“郝铁人”。与早已出名的钢人董河蛮齐名。
武家庄土地盐碱地较多,根据土壤好坏,种有棉花、玉米、高粱、东西花园好地还能种些麦子、虽然产量不高,总算五谷杂粮都有,也算丰衣足食了。直到后来,全家攒钱,买了头老黄牛,才把母亲从种地上解放出来。
说起买地,父亲真是吃尽了苦头,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一般人家谁舍得轻易卖地,那时但凡卖地的,一部分人家是遇上天灾人祸,重病缠身,卖地救人要紧。大部分却是染上了毒瘾,毒瘾上来,便与跟了鬼一般,家中有啥卖啥,那时父亲打短工,虽然挣不了几块钱,但他对自己吃穿都很严苛,钱是只进不出,但要是买地,多出几个钱也行。他常说办正事吃亏也是便宜。
母亲一生,生养过11个孩子,成活了九个女儿,第五个是男孩,为便于养活我,取个小名五妮。女孩窝里男娇养,在家里,凡有好吃好穿,姐妹们都让着我。在那缺吃少穿点个煤油灯全靠手工缝补衣裳纳鞋做袜的年代,生养10个孩子的艰辛真是难以想象。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91岁那年,他还提着箩头给猪羊挑菜割草。他经常教导我们,人不怕穷,但一定要有骨气,再穷再难的日子,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一定能改变。但一定不要染上不良嗜好,染上赌博吸毒,等于慢性自杀,离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便不远了。
父亲终身信奉吃亏是君子占便宜是小人,宁肯他人负我,自己绝不负他人,以至坚持得有点过份。我二姐嫁到本村后,亲家赶着牲口要给我家耕地,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他觉得自己用镢头刨地出点力不算什么,落下亲家人情怕自家姑娘在人家受制。
父亲终身念念不忘的还有几件事,便是感谢收留他的阎恩德老俩口,及多年免费让他居住房屋的主人吉科老人,要不是善良的武家庄人收留他,也许他早就冻饿死在街头。西谷村郝姓本家曾多次唤他回去,但他确实已离不开这儿相亲相爱的村民了。
解放后,村里学校经常请父亲去做忆苦思甜报告,父亲讨吃要饭的苦难童年,艰苦节俭勤劳致富的光荣历史,深深感动教育了一代人。
1986年,奋斗了一生的父亲走完了他艰难苦干的一生,远离我们而去,父亲享年93岁,完全应了对贤人那句“仁者寿”的古语,1990年,享年81岁的母亲也闭上了她慈祥的双眼与父亲团聚去了。
天大地大没有父母亲养育之恩大,父亲母亲将永远活在儿孙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