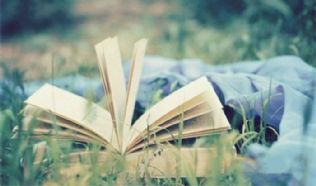
任何伟大写作都是一种艺术的献祭,有个台湾女作家曾经说“小说写到最后,我说把美丽的给予艺术,把丑陋的留给人生,把温柔的给予别人,把暴力的留给自己”。但我们每个读者是否都能够理解作家的这份苦心呢?我看未必。因为年龄、阅历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一些小说,就算它们是业内人士公认的经典作品,但在大众读者这里都会遇冷。因为我们看不懂,于是文学评论家应运而生了。他们可以利用艺术的手术刀,对作品进行由表及里的深入解构,从而引导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作品中,收获豁然开朗的阅读快感。
财经专栏作家徐瑾著称于政商两界,其深厚学养、独特视角和犀利文风,素为人仰。而其散文随笔,亦清新佻脱;感时悟世,远出俗流。业内称其文笔有经济学者的功架,有律师的细致入微,有淘金者的热切和好奇,还有文人的质朴和纯真。徐瑾在最新出版的随笔集《有时》中,涉及了全球炙手可热的作家和电影人,比如太宰治、村上春树、菲茨杰拉德、马尔克斯、王尔德以及徐皓峰、塔可夫斯基和小津安二郎等。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深度剖析,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视角,延伸出来一系列哲思美文。
全书分为爱、衰老和救赎三部分,收录了二十八篇文章。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譬如在《审判王尔德》一文中,徐瑾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明明社会上男风盛行,但人们却容不下一个离经叛道的王尔德。社会将他送进了监狱,从而毁掉了这个异端作家。但王尔德是一个预言者,代表了一个现代的来临。他在法庭上的申辩,与其说是天才人物的不羁,倒不如说是为了无数同性恋者而申辩,甚至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代表了一种人类千百年来对异端审判的控诉。因为给异端宽容空间就是给我们自己进步的阶梯,而让异端有效申辩的权利,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底线。
在关于衰老这个主题中,作者以徐皓峰的小说《道士下山》为标本,旁征博引,剖析了国人对于生老病死的看法及自己的感悟。她说,现代社会吹捧年轻,其实还是浮躁。原因之一是部分老人失去自信意态之后的失态失仪,而据此找到的年轻人无非是迎合老人的投机之辈而已。很多文艺问题,徐瑾都有自己的思考,譬如她说武侠小说真是童话,无法认真对待,金庸是青衫少年,梁羽生是白面书生,古龙则是牯岭街少年。徐皓峰不同,他文字偏向老练,而且整个作品气质是老人视角,这或许和他研究道教有关,也与他接触民国老人有关。像这样的阅读体验,在书中比比皆是,让人顿时耳目一新。
徐瑾读书,能真正读得出好或不好,且能头头是道,下笔成文。读书是门学问,或开卷有益,或一无所获,《有时》的贡献,可以说是方法论上的。《有时》是一种对于生老病死的时态描述,无关价值观与伤春悲秋。书名《有时》引自圣经和合本《传道书》:“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这似乎告诉我们,生命或许就是一个个偶然和必然构成的,不要小看那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偶然,也许它就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