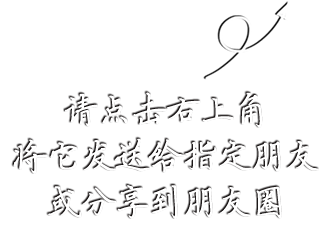这幢住了二十多年的屋子似和我一样也初到中年了?
大概是吧。
太新的房子不会有家的感觉,只是一处新舍,纵然住上几年,梦里的家还是在旧屋。我喜欢老房子,会看着他剥落的墙皮想到旧日,会吹着他不安的窗缝里的风想办法御寒。深吸一口,还有路过青春的空气,出门一步,还有老母琐碎的叮嘱。我又赖在这屋里千多个日夜了。
许是最后一场秋雨罢,它迟迟不愿离开,淅沥到傍晚,又淅沥到我晚饭即眠的梦初醒的午夜。还在滴,还在淅沥,雅致的人会说它是对季节的眷恋,其实也只是助了些凄凉,深秋仍一如既往的枯索。但偏偏我就喜欢散落的钢琴声后阿伦最情深的那一句:有日,让我倚在深秋……几十年来,我一直会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在深秋》!
骄阳在另一季艳过,艳着彤彤的红,更艳着绿以外的迷惘的白,正午酷热得不敢看它,而黄昏的赤白依旧让人流汗,让人无精打采,让人懒散着自己的懒散。所幸已告别了它。想寻一些浪漫,须得秋雨,或再伴几声秋虫的呢哝。秋雨有别于春雨的期待和不成熟,更有别于夏日里骤雨的莽撞,说来就来,不速而至,狼狈到落汤鸡。她凄婉缠绵,不急不燥,在化作雪前会把她最后的美丽不吝不啬地滴给人们。
深秋的掌灯会比夏天早两个钟点,老房的灯绳就那样孤独地垂落着,上半截接近如初的白,下半截早已成了腻黄。逢着落雨,数着人生的无奈,于昏暗中拉响它,骤亮的瞬间我是会想起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我小小的时候,父亲给我一本唐诗贴子:天门中断楚江开……巴山夜雨涨秋池……我常常的写,也生生的记,但根本不懂巴山是不是就是有无梁殿的那座山,更不懂是什么样的情节在李商隐心头盘旋而写出这样的诗。归去来兮,来兮又归去,那本贴子早些年便已寻不见了,父亲也幽居了好多年了,那垂落的灯绳并未换过,那下半截的腻黄或许有些他的手渍罢……且听雨落,会不会有一两声虫鸣?
夜,既深。
在这曾经是鄙野乡间却现在又不算灯红闹市的地方,怕是等不来虫鸣了吧?是已经根本没有秋虫了!不再有砖缝瓦隙的日子里,水泥是比木材更好的建筑材料。可这独怜怜的夜雨还有什么?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扑簌簌……扑簌簌……静听着雨声斯文优雅地轻抚窗外——一位如花的女眷在柔声诉说,慌张根本不是她的神色,看淡的一切和岁月的积淀,她才会匀匀地落,匀匀地作响,如抿着嘴儿在唱蔡琴老歌——是谁?在敲打我窗……渡口旁找不到一束相送的花。的确,秋雨就象蔡琴的老歌,人到中年,波澜不惊,艳过回眸,—味醇香。
房子终究是老些了,想必二楼房顶的油毡和水泥有了龟裂之处。积聚的雨水顺着缝隙往下淌,巴答的雨声足不出户便耳闻了。这萧瑟的夜里便被漏雨声哭笑不得了。妻找了个脸盆就在巴答处,想这绵绵的秋雨概也不会倾盆,高枕无忧吧。雨滴无规律地在落,三两滴掉在盆中央算大珠小珠落玉盘,倘有一滴落在盆沿上,声音便清脆如磬。这些声音伴着我似快要睡着了,凉意微逗的夜,似有一阵阵摇橹声,一阵阵虫鸣狗吠声……
且听秋雨,淋了入夜,湿了清晨,等来银装素裹,若明年又是柳暗花明。人生自有长短,年华何堪苦乐,四十人生大抵如此认为吧。
初寒,不尽,诸君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