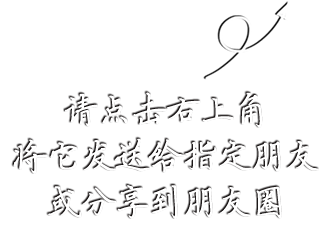一
人们总把故乡称作老家,既亲昵又沧桑,叫得人直揪心。
我的老家南尹是个较大的村,心底,常把它叫大南尹。仅这个“大”,就让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充满了骄傲,这种骄傲在我暂别它之后越发变得浓了。上中学离家住校了,同学问:“你家是哪个村的?”“南尹的!”“哦,人家你们村可是个大村。”每每闻听此言,心里总有一股美的滋味,这是老家给我的一份心灵馈赠。
其实,更让我骄傲的是大南尹的大护村堰和长在大护村堰上的大护村柳。
南尹的护村堰,高不过丈余,宽亦丈余,因它将一个大村环围着,也就理所当然地冠之以大了。堰的上端两侧,便是高高大大的柳,株距近,露出地面的老树根相拥相抱,攲嵌盘屈,不可名状。枝柯犬牙,冠盖交构,参差披拂,浓荫密布,遮天蔽日。垂柳不多见,只间或有之,也就不会给人“万条垂下绿丝绦”和“当风舞婆娑”的诗意联想。没有葛藤攀附,也就没有“蒙络摇缀”的芳姿了。枝条无粗无细,无长无短,或直竖,或旁伸,一力坚挺,硬铮铮傲视碧海苍穹,少有曲线美,倒极像当地农民父老粗犷淳朴而又阳刚不屈的性格。两排柳之间,行距之宽本可行人,也有人行踪迹,然而并没有踩成路,多见的是孩童们散乱而密布成片的脚印,而顺着一片狼藉似的脚印往上瞧,很可能会发现树的顶端有一鸟巢,你可以想到,这鸟巢是怎样吸引孩子们的眼球了,也可想到那昂着的小脑袋和那又巴望又无奈的神态。除此,大人们,虽然每天都到田间劳作,从它身旁走过几次,却是不多来这里的,农家少闲月,柳间闲步是有闲阶级、有闲人的逸致闲情。只有夏日,村民们在附近干活,工间休息时,才来这里,这儿有绿荫遮阳。
南尹小学早先分两个学堂,低年级设在村西的“老爷庙”里,中高年级在南校,当初也是个祠堂。南学堂的后背紧靠护村堰,那一段护村堰是童年时期的我和玩伴们常去的地方。这里,记载着我儿时的童话,儿时的梦。还不到上学年龄,却已“就学堂”了,而且,从后窗户常能传出一个女先生讲课的声音,当然听不懂,不知道她支吾得些什么,却总爱听,那声音柔柔的、甜甜的,听起来很受用。成为白发人之后,我常常想,当了一辈子被称作“猴儿王”的教书匠,难道与还是“猴儿”甚至还没有等到进化成“猴儿”的小时候常去那教书的“鬼地方”有关?可那时并不以为然,因为那地方并不“闹鬼”。在那儿玩得虽然不都有什么名堂,却常常乐而忘食。好多时候是玩土玩泥巴,在堰上挖出个见方三五寸深也三五寸宽的小坑,上面用柳枝柳叶盖上,便是房子了。前面再挖条小沟,往里面撒泡尿,便是门前流水了。把土用尿和成泥,拿在手里把玩,团来团去,再放到有平面的石上或断砖上揉搓一通,捏弄成平底小碗状,平放在手里,然后,翻转手将泥碗向石上或断砖上猛一摔,碗底爆破,发出“叭”一声脆响。这种玩法还真有个形象而又响亮的名,就叫“摔响叭”。谁的“响叭”摔得响,谁得意。然而,我却总也得意不过其他小伙伴,手上的“响叭”摔得始终不那么响亮。到老了我也曾想,一辈子未能成就一鸣惊人的响当当的业绩,究其缘,恐怕也是因了小时候摔不响亮那个“响叭”之故。
更让我得意不起来的是我没有其他伙伴们嘴里一吹就响的柳哨,我们村人叫它“柳鸣”,那是他们的父兄用嫩柳条做的。我父亲死得早,又上无兄长,没人给做,嘴里自然也就响不起来了。每每听到“柳鸣”响,就羡慕人家,索性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又不敢径直回家对母亲说,便偷偷走开到别处了。
护村堰护村柳是本村先民的杰作。初衷大概是用来防水患的,日后却成了此地一道骄人的风景,一道浓绿的亮色。这一亮色,也是故乡给所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南尹人涂上的生命中的第一道视觉底色。有了这道底色,那份故乡情结在心中便凝得再也化解不开了。什么叫牵肠挂肚?这就叫牵肠挂肚!到死也在肠子上牵着,在肚子里挂着!这堰这柳,把村庄围成了个大圆,留有通往八方的八个村口,名副其实的四通八达。外面的世界再大,从四通八达的口出,走四通八达之路,何所不至?吾乡先民的聪颖和可通四面八方的宽阔襟怀,皇天后土可鉴,此堰此柳可证。
二
护村堰、护村柳是南尹的地标。如果走在回村的路上,距村还有十几里,只要地平线上出现黑压压一条林带,黛螺横亘,你心里定会瞬间蒸腾起一股暖意,家就在眼前了,别的村是没有这般奇伟壮美的特色特景的。有它在,游子归来,你不会迷路。见着柳,便会立即生出已然扑入它怀中的感觉。你一定会想到前有稚子候门,也一定会想到母亲妻子的倚闾之望,这样,你旅途的疲劳会顿消,脚底会一路生风,步履会一路轻快,成调或不成调的山西梆子歌也许还会哼几句,“绿水青山带笑颜”,“载欣载奔”。且将那离家的日子里,在外挣扎打拼所积压于心底的块垒和不愉快统统化作子虚,抛于脑后。护村柳,它的巨臂会远远地伸向你,抚摸着你心灵的创痕,慰藉着你的感伤你的倦意。再走近,便不见了那条带的形状,黑压压也不显得黑了,清淡了一些,是绿云葱茏的模样,蓊蓊郁郁,如烟如雾,与心里的暖意一样,有蒸腾的气象。这才是护村柳的真颜真色,真容真貌。
吾乡之俗,没有折柳送行的习惯,但如果你真是离人,走出老远了,它也一定会令你频频回首,让你眼中再现那依依不肯隐去的护村柳。那么,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一个假定和推断了,在遥远的去日——那“去日”,遥远得可用“历史”二字形容了——当你骑着瘦马浪迹天涯,走在愁煞人的古道西风里,当你在夕阳西下时听到枯藤老树上昏鸦的哀叫声,那浮现在你脑海中的护村柳啊,它也一定会倍增你的离情别绪,令你腹内萦回九曲,肝肠寸断,那一条条纵横着的如丝细柳,是母亲脸上为你担忧的泪痕阑干,谁能不动情?情又何以堪?
倘是暮春孟夏,那漫天飞舞着的柳的花絮,早早就撩逗归人的脸了,弄得你直痒痒,眼睛也迷离了。一腔恋乡意,全让这柳的花絮给惹出来了;满怀归客情,都叫这柳的花絮给牵出来了。那么,即使没走累,也坐在村口的护村堰上、护村柳下歇歇脚吧。坐在这里,似乎和无忧的儿时岁月重合了,那意境,那况味,有如走进童话中。烟袅袅,风微微,树香沁鼻,闻一闻也很惬意的。那是柳树特有的香味,就叫它柳香吧。再抓一把脚下的黄土,闻一闻那淡淡的土腥气——啊,不不不,那是泥土香——真好!
如果你正好坐在有绵绵土的地方,就更好了。那乡亲们所称的绵绵土,黄得纯,细得很,抓在手里,觉得柔滑中含有点儿温润,很容易让人想起年轻时的初恋,抓住了女友纤纤的手。
很多年前,那绵绵土还另有妙用。襁褓中的孩子,腿瓣臂弯处常有红斑溃疡出现,那时候,我们那里的农村人还不知道滑石粉为何物,或许,知道也买不起。于是,找些干干净净的绵绵土敷上,也就对付了。不相信?去问老辈人!或者,清明节,爬在母亲坟头,听听母亲的回答!听听她在坐月子——天下所有母亲受难的日子里,是怎样呵护你的。不过我想,母亲一定默然,一定缄口不言,她绝不给你说些什么,母亲是不会将自己的苦处和责任轻易对儿女们诉说的,无言地忍受是母亲的天性。把苦水自己吞下去,把责任自己扛起来——这就是母亲,这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这是世上第一情!这是人间第一爱!这是天下第一真!这是伟大之中的伟大!
南尹的护村柳也有母亲那样的性格,那样的情怀。每个村民都是它的子、它的民。它没日没夜无时无刻地在殷殷守望着他们,拳拳爱抚着他们,眷眷念想着他们。清晨,它把枝头轻轻摇动,唆使翠鸟和鸣,婉啭流泻,给出工田园场圃的人们一份好心情。又是它,把太阳请了出来,给了人们一份温暖,一份光明,一份希望,然后,它便一俯一仰地看护着他们了。狂风来袭,它是挡风的墙;洪水进犯,它是拦洪的坝。傍晚,当太阳平射在它的枝梢时,满世界都是它的影子了,它把阳光点缀得斑驳陆离,煞是好看。那是它在抚摸大地,同时也在抚摸生活在大地上的子民,一边抚摸,一边又亲吻着他们。夜里,它是荷枪而立的战士,在国门哨卡,仔细谛听着远远近近的风吹草动,观望着守护着它心中的吾土吾民。有它的守候,有它的监护,有它的翼蔽,夜更黑更静,大人孩子都有如置身摇篮中,尽可高枕无忧,酣然而睡,进入恬美的梦乡。
记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吧,南尹人才吃上甜甜的深层井水。之前,可以上溯自此地有了第一户落脚生根的烟树人家为始,多少年了,人们一直吃着苦井水,是地地道道的苦里生苦里长,一代又一代的南尹人,就是这样在苦水中繁衍生息苦苦挣扎的。村子里,有两个挺大的积水池塘,村民们叫它水圪沱。水井,紧靠水圪沱。下雨了,村子里的水都往水圪沱里流,再渗到井里,这便是全村的人畜用水。遇有浇地灌田,便把村外的水经村口引进,注入水圪沱,灌得满满的,这一天是全村的盛大节日,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甚至倾巢而出围观相庆,这意味着能吃好多天不怎么苦的水了。南尹的护村堰、护村柳见证着这一切。当引进村的水从它身边淌过时,它也在笑,它也在乐,它一直在和村民们同甘共苦着,此时,它更是在为村民们笑,为村民们乐。现在追忆,那笑声,一定不朗,而且一定是沉沉的,那乐意中,也一定含有几多苦涩的成份。
南尹的护村堰、护村柳记录着南尹人的苦难。它耳边,经常有这样一句话飘过:“能把户口迁出护村堰就行了。”这是家长们鼓励孩子好好念书时的口头禅,像祈祷。一切怨怼,一切悲楚,一切辛酸,一切希冀和寄托,尽都宛然于其中了。大实话,掷地有声。
考上大学后,户口自然也就迁出了护村堰。但是,无论我走出多远,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好像没走出护村堰。那一抹横亘于天地间的烟柳,就是幻化成柳烟,也还在眼前罩着。即使在睡梦中,只要想起了它,便准也想起了母亲;而更多地想起了母亲慈祥的面容和关切的眼神时,那绿柳,那西去太阳下长长的影子也常常清晰地在眼前显现。
三
然而,多少年以后,令我思之不已的护村堰、护村柳却从我眼前消失了,如同更让我思之不已的母亲在我面前消失了一样。这也许是正常的,这世上,只要是生命,就不会不消失。又因为有生命的柳是长在无生命的堰之上的,那护村堰自然也就得受株连。改革开放了,社会进步了,乡村要城镇化了,人们面前的路更多了,四通八达,也许不够了,需要百通百达、万通万达了。你能数得清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以“万通”“万达”命名的公司吗?这也许是好事。村庄在向外拓展延伸,原来护村堰外的地方也盖起了楼房,像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打开一样,有象征封闭嫌疑的护村堰被铲平了,大南尹更大了。
但我想,柳应该是属于乡村的,分明是柳花吹满头的季节,进村时,却不见了柳花飞絮拂面来,无论怎样地超前想象,总免不了寻寻觅觅。其实,柳树随处可见,可哪一株是系我老家情结的呢?哪一株可让我咀嚼乡情呢?
童话犹在,而产生童话的世界已不在;梦境犹在,而孵化梦境的温床已不在。呼不回儿时的骄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便真成了绝唱。今后,南尹人的生命底色该是什么样的呢?绵绵土或许还有,却令我心更“此恨绵绵无绝期”了。那并不得意的“响叭”声犹然在耳,但变得更叫我得意不起来了。向前滚动的历史车轮,快也好,慢也罢,在清理旧日渣滓的同时,总免不了碾碎一些割舍不下的东西,令我梦牵魂绕回环顾盼的老家的护村堰护村柳便是轮下祭品。而今它们已成勾起我作沧桑之忆的“望中犹记”,正像戏文里唱的,“要相见除非是梦里团圆”了。
南尹的护村堰啊,南尹的护村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