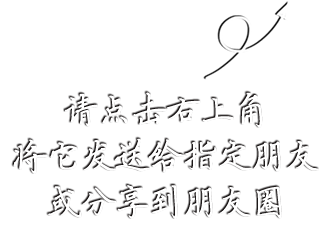固知此行不寻常,涉洋过海,穿林越岭,烟波迢迢,间关重重,不是等闲出游,匪轻匪易,行前也考虑到各种因素,做了诸多方面的思想准备,临了,却知纯属过虑,没有他邦异域的惊讶,没有去国鄙远的神秘,甚至没有殊方歧俗的生疏、局促和警惕,虽不见得就“六合之内,恣心所欲”那么肆无忌惮,遥荡恣睢;那么任心纵散,全无所讳,但心儿里,的确轻松随意,舞雩归咏,只像兴致昂然地到亲戚家串了个门。这是本次台湾行的大体感觉。
阿渠的家人
当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后,陪我们一同前往的名叫任刚的大陆旅行社领队便将全团三十多个成员的整个身家交给台湾导游了。
导游就是阿渠,本名叫蔡国渠,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算不得高大,圆脸,微胖,给人持重敦厚、质朴平淡的感觉,慈眉善目,眼神明亮,对于陌生地的陌生人,我有观人眼度人心的习惯,阅人经验告诉我,这是个心地正直善良的人,也想起了孟子提醒世人的话:“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意思是,了解一个人,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无法遮掩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心术正,那么眼睛就清澈明亮,心术不正,眼睛就会像罩上了一层什么东西似的蒙蒙不清。照此说来,这人值得信赖,我们尽可放心了,毋须心照不宣地警惕什么。“你们就叫我阿渠好了,咱们都是一个民族的子孙,你们都是阿渠的家人。”他说话时声音略显嘶哑,话音未落,关系就拉近许多了,洗刷了人们心头顿处江湖之远的些许风尘倦意。他介绍自己说,在大学原本是学数学的,毕业后,当过中学数学教师,与导游职业根本不搭界,迫于生计干了这个,也就喜欢上了这一行。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确是个资深的导游了。
阿渠是个很健谈也很随和的人,无论在转移途中的车上,还是在景点,都在对着手中话筒不停地讲,他并不迴避那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也不忌谈自己在台对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之间无所偏倚的立场,总想把自己知道的有关台湾的一切都一古脑儿毫无保留地告诉大陆来客。所讲内容涉及面很广,政治、经济、历史、气候、地理、人文、习俗,还要随时应答年轻旅客们类似邓丽君是因了什么而死的这样一些即兴提问。他评论台湾蓝绿两营的状况时,说得也客观,并不偏袒哪一方,褒贬臧否,都是中正的持平之论。公允,中国血统使其然;中庸,中国传统致其然。
阿渠很会调动一车人的情绪,由不得你不听。也许是当过教师的缘故吧,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就必须拥有一桶水的道理,为了当好导游,他读了许多书,查阅了许多资料,做了许多笔记,尽可能地丰富自己,他还曾多次被有关方面请去给接受培训的新导游们讲课。他很敬业,不仅以导游为职业,也视其为为之奋斗的事业。我过去也结识过大陆的一些导游,倒是年轻,作为向导,绰绰有余,不过,也就只能是个向导了。我旅游时,多种情况下,是属“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头来莫名其妙”的那种。这次和阿渠在一起,一改上车睡觉的习惯,专心致志地听讲,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课堂上,当然,有些“传统”是不可丢的。在台湾的最后一天,我曾私下里问阿渠:“你坦率地告诉我,就你掌握的有关资料,这几天来讲了有多少?”他想了一下,说:“大概就是十之一、二吧。”我相信他的话,一桶水,足够。阿渠所讲的内容,知识性很强,让人听了总有心得,他不像大陆一些导游,尽讲一通低俗的噱头哗众取宠。
一次,我滞留于一处购物店,突然发现店里没本团队的人了,赶紧往外走,心想,糟了,又该让快嘴梁申威说我“你又吃榴莲(留恋)了”,出了店门见阿渠正等在那里,有点着急的样子,我忙道歉,可阿渠却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说:“怪我,怪我,是我没有强调出店的时间。”他这一说,并没有令我轻松多少,反倒觉得更不好意思了。
早饭前,大家都得将行李箱拿到所住旅店的一楼大厅,集中一处,方便统一装车,每次下得楼来,都见大厅的醒目处立一标志性牌匾,上面写着:“阿渠的家人”,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旅人,靠拢于此;行李,归拢于此。每天,每地。
儿媳妇教导我说
临行前,儿媳妇将小型数码照相机交给我,“多拍一些吧”。我拿到手里把玩了一阵,看不明白,早一年前还用过的,现在就不行了,想不起该咋使,告诉她:“忘记怎么用了,”她拿过去舞弄了一会儿,便又交到我手上,并教导我说:“我已经设置好了,你只按这个小按钮就行了,开也是它,关也是它,其他的就别管了。”好的,这简单,会用了。于是,小心翼翼地装好,放在行李箱里方便拿取的一角。
在台湾的前几天,就按儿媳妇教导的照办,只动小按钮,开也是它,关也是它,照景,照人,照了许多,更多的是给携来的那个夫人照,老太婆也就根据我的指挥,装模作样表演出了许多造势姿态,笑口常开。——“她好,我也好。”
第四天在阿里山火车站,选好了取景处,我和夫人站在一处,把照相机交给了王福兴:“给我们俩合拍一张,用我们的相机”,于是,先拍了张半身像。由于是近距离,看得清楚,发现他拍照的动作有些不对劲,和我不一样,不都是按那个小按钮,于是纠正他:“错了,错了,你怎么还按那个大按钮呢!”弄得王福兴摸不着头脑,我便正告他:“临行前我儿媳妇曾谆谆教导我说,只按那个小按钮就行了,开也是它,关也是它,不管别的”。他好像弄明白了什么似的,又像指责我做错了什么似地说:“你儿媳妇教导的没错,开机和关机当然是只按这个小按钮了,问题是照相时按的快门是大按钮呀,这还用人家说吗!你这个人呀!”他扫了我一眼,没有恶意,但有取笑之意,又问:“你这几天就一直是这样照的吗?”我说:“是呀!”这傢伙又扫了我一眼:“完了,完了,给我们几个照的也可能没放在里面。”于是,他又舞弄了一通其他按钮,看了看镜面,说:“在台湾的,一张也没有,白白糟蹋了我们的许多表情!”夫人在一旁听着也不答应了:“那我就白照了那么多?”我说:“哪还能咋办?要不回去我给你二毛钱,现在身上没有。”她瞪了我一眼,闭嘴了。王福兴笑了,老太婆也笑了——“他好,我也好。”
回到车上后,弟兄们一个个“金刚怒目”,摆出了“声讨”我的架势,我忙转移话题,调侃道:“哼!还说我呢,我多聪明呀,我比季春说的那个西安市的副市长强多了!”良才不知道杨季春在一次同学小聚时讲的那个故事,于是我给他说,季春在省政府当秘书长那阵,出访德国,同行者中有个西安市副市长,拿着照相机照了一路,后来被人发现他是反用照相机,把伸出的镜头对着自己而将镜面对着所取景物的,这样一路照下来,就只照了个自己的鼻子。
“他不如我吧!”我得意地说。
“人家还照了自己的鼻子,你啥都没照。”夫人揶揄道。
“那好,我今后就多照几杆鼻子。”
在台湾,诸如此类的错误,我还犯过一次,不过,那就与儿媳妇的教导无关了。
车行到东海岸的一家红珊瑚珠宝店,店面很大,我和老伴都相中一款红珊瑚项链,决定买两条,给两个儿媳妇,一人一条。兑换的台币现金不够,得用在大陆特意准备的工商行银联卡,刷卡交易时,我按了两次密码键,均告知所按密码有误,准备再按时,服务生提醒我,你只能再按一次了,如果按错,你的卡可就被锁了,得回大陆解锁后才可用。原来,我经常用着一个密码,来台前,还特意换了个密码,这按键有误,不用说,估计是根本就没有换掉密码,进入老年后,倒是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记性了,那就照原来常用的密码再按一次吧,结果,还是被告知按键有误,完了,啥都买不成了,犹豫了一下,想向其他弟兄们借钱,后来打消了此念,丢人,于是,离柜台而去了。
老伴旋即笑了,苦笑,说:“这一下好了。”
我旋即也笑了,傻笑,说:“这一下好了。”
她接着又说:“省钱了。”
我赶忙也说:“省钱了。”
——“他好,我也好。”
悲风泪雨阿里山
知阿里山其名,最初是因了一首歌,确切地说,只是那首歌的其中几句:“高山青,涧水蓝,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唉……”
就知道这么点儿,其实,最钟情最具吸引我的也只一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就冲这个,心想往之,时日已久。早有一睹阿里山姑娘之美的意思了。
后来又从书中得知,爱国诗人、书法家、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生前曾在日记中留有遗言:“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与之一并流传甚广的还有他的述怀诗《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读来让人悲从中来,黯然神伤,忿忿不已。老先生思乡心切,然而,“君问归期未有期”,回归无日,希冀成灰,空自叹息,唯盼两岸早日统一,亲人得以早日团聚。
于老先生作古后没有葬在阿里山,也没葬在玉山,而是葬在台北县观音山上的。但由于有那么一句葬于阿里山的遗言,还有他催人泪下的诗,我便对阿里山又多几分敬畏之情了。
无论出于哪种原因,今有机会能去阿里山一游,那滋味也是美不胜言的,心情自然舒爽。
由于心里装的多是阿里山姑娘,在车子进入阿里山地界后,便一个劲地翘首,移目窗外,留心着来来往往的姑娘们。这很不好,极容易将旅行其间的凡有美态芳容的女子都当作阿里山姑娘。不过只是心儿里一想而已,底事不可与外人言也。
车子停在阿里山火车站附近的停车场,不再前行,剩下的路,是用厚厚的方形条木铺设架高的人行栈道,据说是为了保护这里的生态环境,怕人们践踏了林木苗圃,于是修了这高架栈道的。这里是森林公园,是自然保护区,自然理当如此小心防范。
进入林区,“木欣欣以向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枝柯扶疏,树冠交错,隐天蔽日,气象万千,阴晴变幻是瞬忽间事。
阿里山林区的主要树种是桧树,亦称桧柏,属柏科。阿里山的桧树,挺拔笔直,绝无曲形枝干,还散发着一种清香味,木质坚硬,呈浅红色,以故,亦称红桧,用它来打造任何木器家具,都是无与伦比的绝好材料。更奇的是,阿里山的红桧多在千年以上,据阿渠讲,这里光两千年以上的桧树原来就有三十余万株,现在仅有三十八株了。是日寇占领时砍伐掉的,阿里山的火车,就是为方便往日本运输这些木材而专修专用的。我们沿途所见的许多黑褐色的那些树桩,都是那时留下的。阿渠还说,仅剩的那三十八株红桧,也是因为有的长在山崖边,用来阻挡高处砍伐下来的树木不被滚到山下才存活下来的。这些树有多高?须远距离仰面九十度方可看到树的上端,还不见的就是树梢;这些树有多粗?须十几人合抱方可围住。阿渠把我们带到一个树桩旁,而他却走进了树桩里,由于风雨的剥蚀和游人的踩踏,树桩的里面已成空地一片,只是周边还留有一些参差不堪的片状残楂,冷森森,黯幽幽,苍凉兮兮地似欲与行人语。阿渠用手中的导游旗指着树桩的周边,从这头到那头,再从这儿到那儿,他在树桩里还须走几步的,须十五人合抱,这是一颗生长了两千七百余年的树。想想吧,十五人才可合抱的,生长了两千七百年的树,笔挺笔挺地直刺云天,那该是何等的高大,何等的气魄!如果还在,还活着,绝对是国宝级的珍贵之物。然而,我现在看到的,却是黑糊糊的断桩,没有泪水只有泪痕的朽木!
民族之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
民族之羞!国家之羞!国人之羞!
此刻,我仿佛看到了在日寇刺刀的威逼下弓着身子坎坎伐木的中国劳工,仿佛看到了盘旋在山道上呼啸而去的一列列装满掠夺所得的火车,也仿佛看到了侵略者那一张张洋洋得意地欢呼嗥叫着的狰狞的魔鬼般的面孔! 我好恨!我这样自语着。我的眼睛湿润了,我背过身子,任泪水滂沱,涕泗纵横。我一向易怒,但我知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刻不怒,枉为华夏子民!此地不怒,枉为中国匹夫!
于是,又想起了我非常崇拜非常敬慕的余秋雨先生,他在《道士塔》一文中曾引用过一个中国青年口气硬硬的几行诗句,那是年轻人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我恨我没有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
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感同身受。
我相信自己,如果生逢彼时,面对民族之敌,我也会与那个年轻人一样,拍案而起投笔从戎勇赴国难“仗剑走天涯”的。这不是什么觉悟问题,这是为一国民的常情常态。也许,我的头,会滚落在外族侵略者的刀下,但是,就是不准夺走老祖宗留下的国宝!也许,这只是匹夫之勇,就算是匹夫之勇,也是无愧天地良心的忠义之勇!亏得我至今仍有这等自信的气血。
阿里山是历史的见证人,在公理的法庭上,他一定曾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控诉过那些日寇的强盗行径,我叩问:你这样做了吗?然而,他无语。我明白了,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公理!那时,我们还很贫弱,就是现在,距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也还不够强大。
下雨了,天公震怒了!阿里山震怒了!雪耻洗辱,这是国人的责任,也是阿里山的回答!
至此,我才理解阿渠带我们来这里的意图。他是在告诫大陆同胞,不要忘记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也许,他就是想让我们来这里大怒一场大痛一场的,他在讲解这一切时声音更加嘶哑,甚至有些哽咽了。是啊,台湾和大陆,大陆和台湾,两岸百姓,原本就是同根生的一奶同胞,我们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负荷,我们也承载着共同的现实责任,我们经历过共同的历史灾难,心怀着共同的国恨家仇,理应有共同的愿望和作为,那就是,国家归一统,人民融一宇,风雨同舟,共御外辱。
于是,我又想,于佑任老先生生前遗愿葬于此地,也许还别有用意的,他是想时时警示国人,也想时时提醒国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在阿里山的行程就止于此,再没有到深山更深处,便原路返回。在返程途中,一路无语,心情沉重至极,像铸了铅。
得知这是块伤心地后,就再也没有着意阿里山的姑娘。
在台湾最后一晚的活动,是逛台北夜市,我对此没多大兴趣,随便走了走,也就回到了约定的等车点,找了个方便休息的地方坐了下来,也想顺便理一理这几天的思绪,无奈总也静不下心来,目不暇接的人流、车流和瞬息万变的周边物景总会时时撞入眼帘,带给我一些新奇的感觉。也就在这时,不远的广场那边,缓缓驶来一辆宣传车,车头两侧,树立着两面五星红旗,是升旗仪式上见的那种大旗,而不是手里摇晃的小型红旗。车顶安装的高音喇叭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嘹亮,令人振奋。一曲毕,又接着播放《歌唱祖国》:“……穿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热泪盈眶。在台北,能听到这样的歌声,真让人激情澎湃,血液沸腾,驻足行注目礼的人很多,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大多是大陆游人。也没有任何警察干预。一点都没有想到,台湾会这样包容,政治环境竟如此宽松。
不仅仅是走了走亲戚,简直就是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