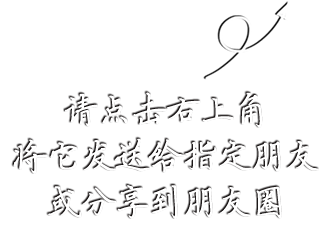下了公共汽车,举目四望,各式水泥建筑参天而立,鳞次栉比,车流滚滚,不时地澎湃着,荡漾着。
母亲因为晕车,弯下腰干呕了一阵。
走吧!父亲说,我记得路,跟我后面!
不多几步,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父亲停下说,我想想啊。母亲说,想什么,说你找不着也没人笑话你。二十多年没来了,啥啥都变样了,你还能想起来?父亲没吭声,急走两步追上前面一个路人就去问。
过马路时,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嘴里念叨着小心小心,仿佛是她拉我,而不是我拉她。她还是把我当孩子,可又步步紧跟我。站在保护者的立场来充当被保护者,这就是我的母亲。
上午十点,医院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正月初七的省城,全然不像农村,过个大年,就像过个长长的懒人节,吃饭,睡觉,打麻将……尽情享福。这里的人行色匆匆,好像压根就没过过什么年。医院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来自山南海北的人,操着各种古怪的方言,熙熙攘攘,穿梭不停,看得人眼睛酸。
穿过人群,来到大厅中央,依稀可见几条蚯蚓一样的队伍蜿蜒逶迤。父亲说,我们各挂各的号,分头行动。母亲说,那怎么行,挂上号先给你看,再给孩子看,我不打紧。
父亲斜了母亲一眼,又没吭声。他知道说不过母亲,只好服从命令。说起来这次来医院,是昨晚母亲一觉醒来后的决定。她给我打电话说,趁这几天闲,去给你爹看看,你眼睛不舒服,也顺便看看。
说来就来了。老俩口起了个大早,“空腹”上路。父亲说,既然来就都看看,也给你妈瞧瞧。没有预约,公交又慢,只好给这慢吞吞的蚯蚓续条小尾巴了。
我说,你们去长椅上坐吧,我来挂号。母亲赶忙接话,对父亲说,你去坐,我和孩子在这儿等。父亲说,那就等谁累了谁去坐吧。
聊着天,时间过得也不慢。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上午的号也基本没了。父亲母亲一个挂内科一个挂妇科,都没号了。眼科有号,我挂上了。
之前所有的争论都显得多余,他们只能陪我去眼科看病。
这一看不要紧,头一项检查结果显示我眼压高,医生建议我住院,要切实诊断是否为青光眼。青光眼致盲率极高,我被吓得半死,当下就准备入院。
父母亲把我送到24层的病房,已经将近一点,本来就是空腹,这会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父亲说,咱们下去吃点东西吧,孩子累了,先让她歇着,我们等会给她捎碗面回来。不知道是因为人多还是医院效率不高,上午没挂上号,下午的B超又都排满了。一切只能等明天了。
他们走了好久还不回来,我吃了点自带的饼干,喝了杯水便躺下了。
那样的好戏,我白白错过了,父亲回来给我说时,我遗憾得差点掉下泪来。
原来,他们出去之后在附近转了转,捡了一家门脸最不起眼的餐馆进去,准备吃些面。父亲问服务员,一碗面多少钱?人家说十块。母亲说,真贵。大米呢?服务员说,大米三块,不过你不能只吃米吧,最便宜的菜一份也要八块呢。言外之意不就是说吃米比吃面还贵吗?母亲向来讨厌这样弯弯绕宰人,索性对服务员说,我跟赵本山一样,只吃米,不吃菜。服务员只好捂着嘴笑着走了。
不一会,饭来了。父亲的面里尽是汤,母亲的米也只有拳头大平平一碗。老俩口顿时吸了一口冷气,都说城里来不得来不得。母亲一气之下叫来了服务员问她,你们本子上印着那么大的碗,怎么端上来就变成了这么小的碗。服务员嘿嘿笑着不答话,母亲硬要她解释一二。有好事者叫来了老板,老板说用这样小的碗才能蒸出香米。母亲还要理论,被父亲制止了。
父亲说,别嫌人家给的少,关键是城里人都减肥,胃口就小,你看,人家哪个嫌少了?农村人就是农村人,长得土,胃口也土啊!现在流行小碗,知道了吧!
饭自然是没有给我捎回来。他们俩还都饿着肚子呢。直到进了我的病房,母亲还在埋怨父亲胳膊肘往外拐,尽替别人说话。什么流行小碗,分明就是坑人么,当别人傻子呀!
我能想到他们在饭店时的情形,母亲气愤、无辜的表情,一句一句振振有词,一定笑痛了不少城里人的肚子。
我说,城里的东西贵,医院门口更贵,可是再贵也得吃了呀!母亲说,那是自然,你看,我给你带回什么了?她笑眯眯地从身后拿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我解开一看,全是方便面,十天都够对付了!
下午我开始做一系列的检查,父亲给我划价交钱,母亲跟着我跑来跑去,寸步不离。结果一项一项出来,喜大于悲。母亲嘴上说尽花冤枉钱,可看她释然了许多。
医院,生命的灾难与天堂。到了医院,钱不再是钱,仿佛只是印着数字的一堆纸。查出的病只要还能治,便是最开心不过的事。管它花多少钱,随便什么价都行。
晚上,母亲算着我这一天花掉的钱,不迭地说,真贵真贵,医院来不得。我经这么一折腾,仿佛瞬间顿悟了,生命诚可贵。我问母亲,什么东西比生命还值钱?母亲说,没有,还是命最贵。我说,那就对了,医院是买命的地方,自然最贵了!母亲说,也是,有的人想买都未必能买回来呢,就别心疼那些钱了。
晚上一顿三个人消灭了三袋泡面,三根火腿肠,父亲打了个响亮的饱嗝,母亲笑着说,瞧,这两块钱的面比十块钱的还多,吃着多舒服!
晚上,父亲睡折叠床,我和母亲挤在一张病床上。母亲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说住在24层楼上,就好像把人悬在半空,简直跟上了“马航”一样,忒不踏实。
我知道母亲担心什么,我和父亲,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爱我们胜过她自己。城市的夜空总与灯火暧昧着,必然是无休止的聒噪与癫狂。住在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鸽笼中的人,每一息光亮都瞒不过人的眼睛,各自在寂静中喧闹着彼此,璀璨繁华的帘幕,背后必然是太多太多的纷扰是非,看久了让人觉得累。
我和母亲头抱脚两头睡。朦胧中,我感觉母亲在轻轻摸我的脚。就像我摸我自己孩子的脚一样。孩子的脚柔软细嫩,摸着舒服,可我的脚,长年穿高跟鞋,脚掌上是又厚又硬的老茧。而母亲的手,也是砂纸一般,粗粝不堪。
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一首读过的诗:
给母亲做一回母亲
给她买最好的玩具
天天做好饭菜叫她吃
……
如果有人欺负她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非撸起袖子
狠狠地揍狗日的一顿
……
这一刻,我真的掉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