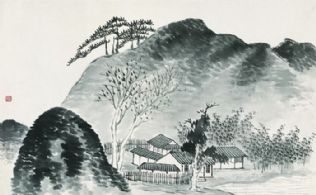
相对于世界而言,人是一本书,故乡是人生的第一章。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村庄就是庄稼包围的地方,因为我家住在村子西南,我外婆家在西南面王答村东北,从我家到她家,在我的印象里,不分四季,一路上永远是绿油油的比人高的玉米。出我们村的时候,走的是村西的坝堰;进外婆村的时候,走的是田间的小路,因为顺路要去看驻扎在他们村菜地里看守那些西红柿、茄子、辣椒、黄瓜或西葫芦等等的外公。我很小,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玉米修长的叶子一路扫过去,开始觉得好玩,后来知道可恨,因为有时候会被划在脸上或胳膊上,隐隐生疼。
我还没有走出过农村的时候,就知道,村庄要有水塘水渠甚至要有河。我家西面,就是一个水塘;隔过坝堰和一小块玉米地,就是水渠;而村北就是潇河。不明白那时候水怎么会那么多。经常没完没了地下雨,下到屋漏涟涟,家里的锅碗瓢盆全拿来搁炕上和箱柜上接雨水。有一天我早上醒来,发现地上的水漫到炕沿的一半,家里能飘起来的东西,都浮在水面上。水塘和水渠里的水,自然逢雨必涨,来来去去路过时,深得让人害怕。但是总有水落岸出让人亲近的时候。那时,鱼呀蝌蚪呀青蛙呀蜻蜓呀,各种水族成员或它们的亲朋好友,按时趁分而来,无比热闹。而我们也无比兴奋和勤奋,虽然父母们三令五申威逼利诱不准近水,但这个方面,让我们乖乖顺服那是不可能的事。当我们今天把一串蜻蜓明天把一盆蝌蚪拿回家喂鸡的时候,他们不见得看不见,只不过他们不可能把小孩像钥匙一样拴在腰带上,也不可能像抓了贼一样天天打,而人也都安然在此,只好装作不晓得罢了。
我们在村西的水塘练了胆量,后来就竟敢挑战村北的潇河了。潇河是我多次提到的地方,它的丰腴、幽美和平静提供了无限的诗意和欢乐,并纵容了我的胆大妄为,它基本上占据了我的绝大部分童年,也就是说,它可能滋养了我的性格。其实不多年之前,我对它的感情与从中国地图上看到额尔齐斯河或淮河是一样的,只是在我转了一些地方之后,才意识到它于家乡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人在逐渐老去,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逐渐理解家乡与人的关系,也更加怀念童年。
到我上学的时候,我知道了村庄里应该有学校及通往学校的路。这两种事物使得村庄生动深刻起来。学校让我明白了部分人情事理,人的奸猾与忠厚,人的聪明与愚笨,人的机敏与迟钝,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能反映出来,虽然这些是我忆起当时的玩伴的时候才想到的,但那时确实是已经表现出来了。通往学校的路也教了我部分人情事理。路上要过许多人家的门。有一家,很大的院子,院子里长满枣树和枸杞,但只有两位老人居住。老人常常坐在门口,都很和蔼。枣和枸杞成熟的季节,他们会主动摘给我们吃;有时候他们不在门口,我们自己跑进院子里采摘,他们也没有呵斥过。有一家,拱形大院门,院子里住着兄弟俩家人,哥哥的妻子死后,续娶了一个山里来的女人,经常被弟媳欺负,连她的儿子也受累。还有一家人,有点傻气,有一年让人写好春联,贴出来后引得大家好一阵笑,上联:新鞋新帽新衣裳,下联:饺子油糕片儿汤。当然内容是好的,只是贴在大门上总不如贴在厨房门上妥当。
我从幼儿园到初中毕业,一日三出勤,来来去去晃荡在村里的路上,学校里学的东西不记得多少,道听途说的人事,还记得很多,比如走街串巷的小贩们的吆喝,谈恋爱的后生姑娘闹了别扭或者李家女儿王家孙子考上了大学。这样的偏歪,用我妈的话说是“正经地方没有,歪门邪道就显出你了”。就是这样的脾性。但我现在虽也后悔学业无成,却也庆幸能有可供回忆的东西。
现在我常回家,也经常在外面碰到村里人。年长或是同龄的人都可以认出,一时想不起姓名,过一会儿也会记起,甚至记起他们家的老辈或小辈。小一点的年轻人,还可根据相貌来揣测是谁家的孩子。但再小一点的,就无论如何都没有瓜葛了。当然,从那边看过来,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虽然那里是生你养你的故乡,它养育你,塑造你,丰富你,成就你,但总有一天,它会变得与你无关。
人必定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收纳所有然后一无所有。
这很残酷。
但人也是一本书,从第一章到末一章,连贯曲折相对完整。
故乡是第一章,它为我们做了铺垫并奠定了此生的感情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