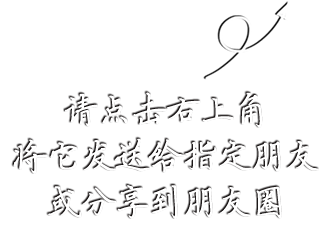中元节那天,忽然想到下个月这天又是中秋节了。我跟一个朋友说:“怎么又中秋了呢?我觉得刚刚过了年啊!”他说:“人老了就是这样啊,所说的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我感慨了良久,心里极不舒服。
今天偶然走在校园东面的小树林里。石板路上铺了一层凋落的槐花,一地细碎干枯的花瓣,走上去发出细微的声响。抬头看树上,花穗上偶尔一两朵残花,倒是结了大把大把的豆荚,鲜绿发亮,翡翠一般。看了看整个园子,柳叶由嫩黄变得枯黄,松柏由嫩绿变得焦绿,山桃树叶开始变红,浆果树也又结满果实了,而墙外的高层拔地而起,已经在封顶了。
冬天雪后,我穿了大红棉衣,在这里留影;初春季节,我打这儿经过,盼着柳树发芽;夏天雨后,我在树荫里散步,惊奇地发现树周围草丛里长了许多蘑菇。心情和场景,恍惚在昨天,但秋天分明是要来了。
时间,它都到哪儿了呢?
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一位大学生理解不了为何时间时快时慢。爱因斯坦为他解释说:“朋友,当你夏天坐在一个火炉旁,你会觉得一分钟是一小时,而当你和钟情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就像一分钟,难道不是这样么?”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两个月之前的现在,不知道多少人沉浸在世界杯的狂热中。我这样的老妇,半夜爬起来看比赛。巴西和德国半决赛,进到第四个球的时候,我自己都蒙了,短暂的愣怔之后,一个劲儿地说德国不要进球了。家人取笑我,说看来我并不是德国的球迷。我反驳说,球员们太苦了,比赛结束后巴西的队员们怎么承受呢。当天早上,我睡到八点多醒来,睁开眼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昨晚的比赛不会是一场梦吧。
在自家球场上,球员们的黯然神伤真让人难受。
然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无论球迷还是球员。
前天偶遇一个同学。当初热火朝天地恋爱,跟另一个女生争风吃醋而获胜。我记得年轻的女孩掩饰不住内心的激情,坐立不安,心不在焉,无论什么话题,她都能引伸到她关注的那个人身上。一次我碰见那个男孩骑自行车载着她,她一脸甜蜜地坐在后面。他们从我身边风一样驶过,我的目光追着看了很久。从那以后,我以为一生一世的爱情就是那个样子。结婚前,她为我展示她的新嫁衣,一件一件地试穿,一次一次地憧憬,簇新喜气的衣衫衬托着她兴奋的脸,像一朵饱满娇羞的扶桑。这青春的爱情让人嫉妒。
然而,他们分手了,很快地,彼此各自成家。
昨天,有一位陌生的母亲,她怯声地向我打听怎么就能让她儿子插班补课。我说补课就要结束了,没有必要了。她说他们是外地来复读的,怕她儿子听不懂这里的话,想适应一下。又说他们已经租了房子住下来,可不可以中午在学校休息,晚上回家里。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她说她有病,不方便做饭。我说让他一个人来就行了呀。她说她已经陪读三年了,不放心。我笑说:“你想要个什么结果呢?”她讪讪地笑笑,不再说什么。
天下母亲,真是太艰难了。
然而,母子一场,最终又会怎样呢?
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在时间里质变,如同凋落的槐花,枯黄的树叶。悲也罢,喜也罢,那个心理时间,不过一个幻觉。事实是,不管炎热里守着火炉,还是和钟情的人在一起,时间,它都悄无声息地不见了。
那些沉淀下来的,智慧、从容或者平静,就是看得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