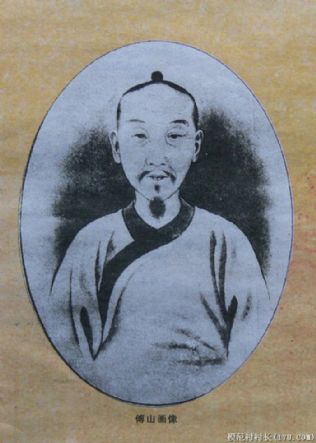
昨日教学生“傅”字,学生组词,竟有一学生脱口而出“傅山”!惊讶之余,我便让他继续往下说。他说他读过傅山先生的一些文章,评价此人很有个性。我越发感到震惊,仅仅一个小学生竟有如此见地,不禁颇生感慨,因为我对傅山先生也有自己的理解,今日不禁又找到先生的小诗来拜读。傅山诗真个性,用我们现代人的话说就是“圪寥”,诗如其人。这圪寥的含义还真不是一言半语能说得清楚的。现拣一首不太圪寥的小诗抄录于下。
春晓
桃花放小红,梨花坠老雪。
黄莺选好枝,睨脘唱晓月。
原诗无题,是笔者根据诗意加上去的。
这首小诗节奏轻快,形象逼真,读过之后,好像听到了春天的声音,看到了春天的面容。遣词极妙,像“放”、“坠”,花儿有了动态;“小红”、“老雪”,形态逼真;“选”“唱”,尤现诗意。四句都是写景,奇的是句句景中寓意。从诗意看,这首小诗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应该是傅山先生的青少年之作。
春天了,汾河水暖桃梨知。那河畔的小桃,绿萼初破,苞尖尖上抿着小嘴的花瓣半露,迎风荡漾摇曳。梨花已经谢了,那发了蔫的花骨朵像积久的雪,脱蒂坠落,留下了已经孕育成形了的子实。春天了,阔别了一冬的黄莺儿已经飞回来了,在枝叶间传来传去,选择最好的栖息枝头,放开喉咙,千啭莺声,浴晨曦,唱晓月。晓月,指农历朔日(初一)之晨,日月同时在天空出现。诗境畅人心怀,引人入胜。这姑且不去说它,单说这“圪廖”吧!
句中的“华”(huā)、“花”,异体同音同义。古时木花叫华,草花叫荣。《诗·周南·桃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句,华,木花也。东晋·陶潜《桃花源诗》有“草荣知节和”句,荣,草花也。到南北朝时出现了“花”字,华、荣归类为“花”。如范云《别诗》有“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句。之后就统称花了。傅山先生把(桃)花写作“华”是顾及不与(梨)花重复的缘故吧?
“睨脘”何意呢?《辞海》注释说:“睨脘,形容声音清和圆转。”据此,睨脘是形容词。《诗经》(山西古迹版)注释说:“睨脘,鸟婉转的鸣叫声。”据此,睨脘是名词。
它们注释的同是《诗·邶风·凯风》“睨脘黄鸟,载好其音”句,释义却相左。在一个位置的同一个词只有一个词性。傅山先生在这里用的是什么词性呢?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里赞美王之涣《登鹳雀楼》一诗说:“四句结对……”照此要求,上句黄莺是名词,下句对仗的睨脘也是名次。名词的睨脘是鸟儿啼叫的声音。这就与对仗、诗境,以及下一句的“唱”全通了。
说莺啼,还有恰恰。甚至叽叽喳喳,那是麻雀的叫声。遣词以准确为准绳,还有什么词能比睨脘更准确,更好的呢?其实,略窥名人诗句这种“圪廖”也不少。君不见李白《蜀道难》里有“飞湍瀑流争喧豗”句吗?
合上书细细想来,我的这位学生难道不是有个性的“圪廖”之人吗?就是这“圪廖”带他走进另一片天地,就是这“圪廖”让他有同龄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就是这“圪廖”会成就一个新的傅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