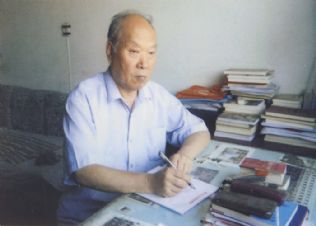


人都有老的时候,老年后做什么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有人爱好打牌,有人爱好旅游,有人爱好谈天,有人爱好吃喝,有人爱好打拳,而我却爱好读书写作,觉得读书写作很有趣味,可以知道古今中外的各种事情。
109岁的周有光老寿星说:“人与其他动物不同,是需要知识的动物,同时也是有思考能力的特殊动物,人通过读书获得大量知识。”他还为《文汇读书周报》题词:“人是追求知识的动物”。我很赞成周老的观点,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必须不断地读书,要活到老学到老,同时要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就需要写作,越活头脑越清醒,越活知识越丰富,越老越将自己知道的知识传播给后代,让子孙后代的生活也过得丰富多彩,这是我们老年人的任务与责任也。所以,我觉得“文化养老,其乐无穷。”
十六年出十六本书很平常
我给《清徐》写了篇稿子《我与〈清徐〉的友谊》。在向永红社长征求意见时,他看到我退休后出了十六本书很惊讶。我是1998年退休的,至2013年,前后出了十六本书,平均一年出一本,我觉得这很平常,不必惊讶。这十六本书,有十本全是我的文章,其余六本是我编的,有我的文章,也有同志们的文章,最厚的41万多字,薄的10多万字,总共160多万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书中有7本是我自费印刷的,花了几万块钱,其余是由县政协、县史志办、集义乡等单位印刷的。有人说要花钱买健康,大买保健品。我花钱印书,也是买健康嘛。我觉得写书出书并不难,会写文章就可以出书,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2000年,韩石山先生在《太原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语言与文字是统一的,书本不过是有字的本子,只要不是违犯国家有关法规,一个人想自己出本书,印上几十本送给师生亲友看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办法是,先整理好书稿,到街上选一家条件好的打字社,花上几百块钱,可印出百十本。只要设计得好,裁得齐,订得牢,看上去一点也不寒碜。”我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出了第一本书,名曰《中庸堂随笔》,印了50本。但是,出了第一本,便想出第二本,上了瘾似的,收不住了。从此后,每年出一本,一直出了十六本,我也八十岁了,精力不足了,才收了摊子。
第一本书是铅字印刷,请康守旺先生题写了个书名,三十二开本,单色印刷,黄色书皮。第二本变为红色书皮,第三本变为蓝色书皮,还在插页上加了国画式插图。后来就觉得这种书有点太单调了,到第五本《休闲杂谈》,便请刘永成先生设计了封面,变为大三十二开,并在书前加了彩色插页,版面装帧也有了设计,加了眉线,字体因文章而有所变化,印出来觉得与书店出售的书没有什么两样了,心里美滋滋的,很惬意。
退休后是写作的黄金时期
我觉得退休后是写作的黄金时期,理由有三:第一,时间充裕。在职时,工作由单位安排,写作要抽业余时间,而且不能影响正常工作。退休后,成了自己的天下,写作的时间很充裕。不用向谁请示,想写什么写什么,什么时间看书读报,什么时间走访文友,什么时间到那里调查,全由自己安排。人老了,象我没有老人,孩子们都成人了,不需要我操心了,我的时间就是看书读报,写作出书了。第二,精力充沛。刚退休六十多岁,身体没什么毛病,一二十年内,精力还充沛的,况且,人们讲养生,我觉得文化是养生的最好手段,看书写作,心胸开阔,不怨天忧人,头脑常是畅畅亮亮,这就反过来又成为读书写作的良好环境,精力更加充沛了。
第三,有写作的经验。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作,走了许多地方,办了许多事情,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有顺利的时期也遇到过逆境,这些都是写作的内容,再加上看书读报看电视,分析世道的变化,写作便觉得心应手,能顺应潮流,适应当前形势,不会逆历史而动。写出来的东西,既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给人们以正能量。我觉得退休后的二十年内是写作的黄金时期,一定要紧紧抓住,用心地、不间断地努力去写,不将宝贵的光阴浪费掉,这样便有了十六本书的结果。
读书写作好处多
前面我写了退休后读书写作的情况,那么读书写作有什么好处呢?想了一下觉得有以下三条:
第一,可以健脑,身体好。你看哪一个老年作家得老年痴呆症呢?而且多为老寿星,巴金活了100岁,季羡林、冰心都活了90多,近百岁。文前说的周有光,100多岁还出书,109岁还为《文汇读书周刊》题词呢。有一篇文章中说,阅读是一种习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一种境界。明代诗人于谦在《观书》中写到:“书卷多情化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容,未信我庐别有春。”看书看得把环境和心身都变好了。这就是说,读书不但增长知识,对修身养性也大有好处。培根在《论读书》中说:“读书使人充实。”我说,读书写作应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一味最好的保健药,以书为乐,勤于动脑,经常动手,活得明白,活得健康,悠乐自在。
第三,可以交友,不孤独。经常参加老龄委组织的读书会,多与文友交流,以文会友,互相切磋,有时会吵得面红耳赤,有时会谈得废寝忘食,但谈清一个问题,弄明一件事情,就会觉得身轻气爽,比吃了一付良药强多了。我看过一篇文章,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当年受到撤职处分后,心情十分烦恼。但一头扎入图书馆后,每天读书不辍,渐渐地看进去了,人走出来了。一个多月积累了100多万字的资料,拟出五六万字的写作题纲,后来又去多个省份调查研究,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写作,既疗了伤治了病,又出了成果,这就是读书写作的功能。
第三,可以发挥余热,为社会服务。我退休后,先后写了《集义李氏家谱》、《集义村志》、《集义乡志》、《龙林山志》、《清徐军事志》、《清源古城》、《清徐碑碣》、《金石文字录注》等地方史志书籍,还帮助郭思爱同志写了回忆录。在我的《中庸堂随笔》、《中庸堂乱弹》、《休闲漫笔》、《休闲杂谈》、《古今集》、《晚霞集》等书籍中,还写了《悉尼奥运壮国威》、《李洪志十恶不赦》、《漫谈孝道》、《救救东湖》、《欺树有罪》等褒扬兴事与鞭挞丑恶的文章,常为人民鼓与呼。这些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在书中写出来,总觉得自己没有白来世上一回,老了也没有成为人们讨厌的累赘,而且还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走在街上也觉得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