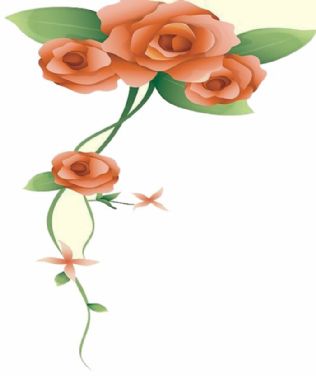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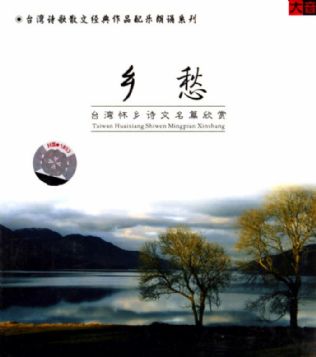
今年春节,又未能回老家与母亲、弟妹们一起守岁过年。
大年初一,值班。
先给三弟打去祝福电话,给母亲拜年。
三弟家比较宽敞,一到冬天,母亲便过去住。若有幸回去,就会与母亲、二弟、三弟一同欢天喜地过大年。
拜了年,电话放下了,可记忆的乡愁升起来了,尤其是那浓浓的、醇厚的味觉乡愁分外清晰地弥散开来。
小飨、叩礼馍馍、摊馍、炉拨、秃玉茭……一股脑儿冒了出来。
老家把走亲戚叫做踅亲戚,踅是来回走的意思,就是在你来我往中拉近、拉紧的亲情。叫得多么醇美、贴切。而小飨就是让踅亲戚者一进门即可受用的美食。小飨用面粉、白糖揉和,用食油炸出的圈状、风车状、片状食品,集甜、香、酥、脆于一体,不用加热,即来即食。那时交通不发达,踅亲戚大多靠步行,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进门就可享用。叫做小飨,真是一个爽切。
大年初二,到奶奶家拜年,是家中的惯例。奶奶念叨着,让三叔到村口接我们。远远地,看见了三叔,三叔也看见了我们,我头一个冲到三叔跟前,让三叔背着或马架着。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快到奶奶大门口了,立马从三叔身上滑下,甜甜地喊着奶奶、奶奶,掀起暖帐,钻到奶奶怀里,嚷着要吃叩礼馍馍。所谓叩礼馍馍,就是长辈给晚辈准备的,里面放有钢镚儿等寓意吉祥的馍馍。或许是奶奶偏心,专门做了标记,要不每年我的叩礼馍馍总会有钢镚儿。奶奶乐呵呵地说,我的长孙今年又出息了。
摊馍是老家的特有食品。走过不少地方,没在其它地方见过。它也是年关才准备的。将当年的小米用水浸泡之后,到村中的小磨盘上磨成浆。磨是石磨,脸盆般大小。将一勺泡好的小米连汤带水倒进磨眼,手握磨把转圈,磨成的浆顺着磨盘的凹槽,缓缓流进下面的容器里。然后倒入小缸或小罐里,置炉火边。待其发酵后,放入碱面,在炉火上支起摊馍鏊,便可摊摊馍了。鏊子三只脚,碗口大小,周边深陷中间鼓起,凹凸分明。鏊子烧热后,抹油,舀米浆摊入鏊中,盖盖儿焐三五分钟,一个四周厚、中间薄、金灿灿的摊馍就做成了。看上去,竟意涵着唐朝美人杨玉环的风韵。
摊馍通常不是现吃,多存放起来做炉拨。
做炉拨,取几个摊馍,再取几个馍馍,将其一刀一刀切成片状。菜也要准备停当。主菜大白菜,此外还要切点胡萝卜片,准备些豆芽。炒菜时,配菜就多了:粉条,木耳,丸子,海带丝,五花肉等等。菜有七分熟了,将馍片、摊馍片均匀地摊放其上,然后盖盖儿焖几分钟。等菜收了汤,开盖儿后,通常还要滴上香烟,撒一些蒜苗丝,搅拌均匀。这样,一锅炉拨便大功告成。
玉茭粒去皮之后便是所谓的秃玉茭。还记得跟姥姥到碾上碾秃玉茭的情形。姥姥将新玉茭倒入碾上顺势摊开,她在内侧,我在外侧,推着碾杆,不时将水洒在碾盘的玉茭上,推几圈下来,晾干,用簸箕将玉茭皮簸出,秃玉茭就做好了。看着这加工成的玉茭,没有了棱角,名之曰“秃玉茭”,觉着俗,却涵着雅。熬秃玉茭最费功夫,需要文火慢煮。母亲说,熬秃玉茭搭配红豆、绿豆、花生、红薯味道会更醇香。
每次过年回家,都可吃到香甜的小飨、可口的炉拨,喝上利口消食的秃玉茭。每次回来,母亲、弟妹们都要给我们带上。潜移默化中,妻子也掌握了做炉拨、熬秃玉茭的秘籍,也成为儿子的美食。
我沉浸在醇厚的乡愁里。外面又响起了鞭炮声——不知不觉已近中午了。
如今奶奶走了,前些年爸爸也走了。
母亲过年见不到她的大儿子,她会更想我的吧。
人们对老家有许多记忆,而味觉记忆可能是最顽强的一种。老家过年的美食被老家人这么称呼由来已久,我却不知道落到纸上的写法是否正确。不过,享受这种乡愁,老家便通过我的舌尖得到回味,弥漫成一种人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