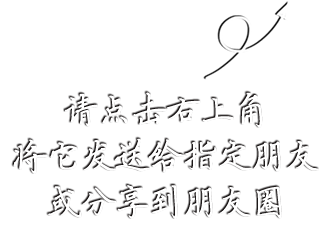夏的来临带来了炽热,槐荫把遭受骄阳炙烤的人们吸引到他们的巨伞下。中饭时分,已是两番劳作的人们端着粗大的“平遥碗”,碗里装着满满的食物,走出各自的院门,朝向槐荫遮蔽的树下,或蹲,或坐,或站,一边用筷子扒拉着碗中的食物,迅速地塞进嘴里,撑得两腮鼓鼓的。至于姿仪外表都没什么讲究了。男人们赤裸着上身,腰里挂一条汗渍斑斑的短裤。女人们上身遮一条二股筋的背心,裸露着粗硕的臂膀和腰围。有的女人毫无羞怯地撩起背心,裸露出硕大的乳房给孩子喂奶。填饱了肚子的男人们悠闲地摘下脖子上挂着旱烟袋,把烟锅伸进烟袋里,大拇指在袋外揉捏着袋里的烟锅,装满填实烟叶,拽出来,“哧”地划着一根“洋火”,点燃了烟锅里的烟叶,嘴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一口浓浓的烟雾从他们的嘴里释放出来。这是他们最为闲适惬意的时刻。那只粗大的平遥碗照例放在身边,不会送回家,因为那是女人的事,理由是女人们要洗碗,她们自然会来收拾碗的。一会,女人就站在街门口粗声大气地高喊“嗨,还吃不吃?”男人闲散地抬抬眼,从占满烟嘴的口里含混地吐出几个字来,“不吃了。”“天天就是个这,就等人荷碗的呢。”女人很不耐烦,但终于无可奈何,还得自己去取。女人气鼓鼓的,胸前的两大奶子更是一鼓一鼓的,肥大的臀夸张地凸显在男人们的视野里。疯嘴的男人们免不了要疯几句,“哎呀,看那膘水,炕儿也得多盘几回。”女人便回敬道:“你也就看看吧,香煞你,知道你也不待见你的那斯干骨瘦”。引来一阵哄笑。
夜晚槐荫把清凉和宁谧交给了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清爽的微风鼓舞起槐荫的索索细语,和身躺在槐荫下沙地上的人们瞅瞅几眼高远的星星,眨几眨眼,终于落下了眼睛的帷幕,发出了甜美的鼾声。秋的萧瑟如约而至,圆而小的槐叶在秋寒的授意下离开了枝头,飘飘洒洒,落在沙地上,铺成一层金黄。狂野的秋风摧枯拉朽一般释放着淫威,摇晃着光秃秃的枝桠,等待冬的来临。
冬日,除了西北风啸叫的日子,除了雪花飘洒的时候,也有日暖风和的时候。太阳挂在低矮的南天,没有一点风的影踪,几个披着老羊皮的老头蹲在槐根下,两手袖在肥大的皮袄袖子里。大概阴冷的屋子已让他们感到厌倦,想出来晒晒太阳,槐树下背风向阳,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今儿这天气好啊,你们早出来了?”刚来的一位与早到的几个打着招呼,紧挨着那几个蹲了下来。其中的一个老羊皮说话了:“多日子没见你,我还以为你去村外听蛐蛐叫去了呢。”“听也得把你叫上一块去,我舍不得扔下你啊。”隔了一会又道:“不熨帖了几天。”另一位开口道:“哦,原来是守了几天儿媳妇啊。”刚来的这位回道:“你不用媳妇子守,可是媳妇子守着你,守也守不住。”其中的一个道:“媳妇子是怕他把东西倒腾给了相好的了。”另一个又道:“能守就让他们多守几天吧,咱们临梢末尾还能赶上这个好时候。”几个附和道:“时候是个好时候,一月一月公家给的生活费,种地不用花地亩钱,哪个朝代种地不纳粮啊?“起码咱不用伸手向人家讨厌了。”几个你一言我一语,言语间透着满足,透着舒心。
又打春了,很快年节来了,槐树下闹起了红火,劳累了一年的人们以他们特有的粗放和愚蛮,在锣鼓的喧闹中宣示着新的希望。槐枝头已长满了饱满的芽儿,兆示着来年的槐荫将更浓更密更繁盛,隐蔽这槐荫下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