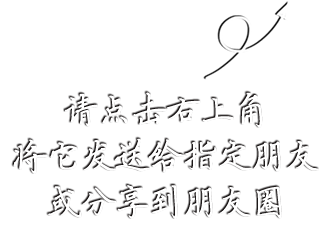“武文潇小朋友,请你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心一凛,意识在一瞬间发生混乱,感觉老师不是在叫我的孩子,而是在叫我。我能感觉到,在那一刻,我迎向老师的温柔恳切的目光中透着多少不自信。我多么希望她收回成命,或者说,也可以让你的妈妈回答。然而,耳畔,掌声已经响起,老师的手已经伸向了我的孩子。
她是我孩子的班主任,年轻,漂亮,活泼,亲切。只见她优雅地蹲了下来,一只手将孩子揽入了怀中。然后,轻轻在她耳边说,说吧,我叫武文潇,三岁了。
我多么希望奇迹发生,她能按老师说的,流利地重复出这句话。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们都满怀期待地看着她,他们似乎毫不怀疑老师点到的孩子会被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难住。
她不说话,只定定地看着老师,那生气而无助的眼神告诉我,她根本就不想理会老师在说些什么,甚至仿佛在说,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搂着我?终于,她的眼皮涨得通红,一只小手“啪”甩到了老师的脸上。年轻的老师猝不及防,本能地松开了手。武文潇便飞快地跑回到了我的身边。
所有的人都笑了,老师惨白着脸也笑了。
这是武文潇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这是老师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当我听完后面的小朋友一个接一个流利的自我介绍后,我发誓再不会骄傲于武文潇的那一点点本事了。三岁,会背四十多首唐诗,三字经可以背出三分之一,数字也基本可以数到一百。但是,此刻,眼前的事实胜于一切雄辩。作为孩子的妈妈,我竟然没有教会自己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武文潇,她现在是一个多么调皮捣蛋的孩子。记得前几天,我还在家里一再地跟她说,记住,上了幼儿园,大家就会喊你的大名,人家叫你武文潇,你要答应啊。于是,我朝她喊,武文潇!她却眨眨眼,鬼精灵般地一笑,说,喜羊羊!
武文潇!
喜羊羊!
……
我们母女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单调重复。我知道她是故意的,这样说下去又有什么意义。于是乎,这个话题只好作罢。也许,我真是太纵着她了。家里雪白的墙壁上,她稍稍趁人不注意,便拿圆珠笔在上面画,见我生气了,又是笑又是跑,吃饭,总是让我喂。不喂,便不吃。不光喂,还得随她这个卧室跑到那个卧室,或者,一边给她唱歌,或者,和她一起拼图。
总是这样,直到看到和她同龄的小朋友自己拿勺吃饭,我才猛然醒悟,我的爱到底给她带来的是什么。
三十岁得子,如获至宝。半生的希望,随着她的降生,迅速做了转移。爱她,给她我能给的一切。只愿看到她健康快乐地成长。她的每一点长进,都让我欣慰无比。夜晚,当她熟睡时,抚过她的每一寸肌肤,那样的柔嫩,光洁而紧致,完美的无懈可击;还有那长长的睫毛,玲珑的口鼻,让我千万次的讶异于造物主的神奇,基因的神秘,千万次的感动不能自已。
原本,她是个多么懂事乖巧的孩子。去年夏天,两岁的她,还整日流连于街头的摇摇车,待到今年夏天,无论如何都不要坐了。只因她的爸爸说了一句“投进去的硬币是再不会跑出来的”。手机响了,总是她到处地帮我找,然后飞快地递到我的手上;无论走到何地,稚嫩的声音总会在第一时间到达耳畔。电话那头,那小巧的双手总不会拨错妈妈的号码。
两岁时,喜欢看儿歌频道。一回家,便吵着要开电脑。如今,似乎对这些毫无新意的东西不感兴趣了。晚餐后坐到床上,不是缠着爸妈讲故事,便是认真地读唐诗,一字一句,美如珠玑!
三岁。寒来暑往整三载。三年的成就,胜于以往所有。小小的年纪,一切都是崭新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小熊故事机中唱出的《聪明的一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连我都辨不出准确的歌词,她却可以全部唱出,而且几乎字句不差!出门时,自问一句忘带什么了?小眼睛一转,即刻便会说,“垃圾!”还有背那厚厚的唐诗长长的三字经,总是字句不乱,一气呵成,真真让人慨叹之至,望尘莫及。
一次,翻出了旧时的照片。小小的黑白相片上,是三岁时的我。我将它拿给我的孩子,问她,这是谁?她毫不犹豫地说,是亲妞(她的小名)!我再细看,那小脸,那眼神,岂不真是一模一样!
看着她,常常会陷入一种“是我,非我”的遐思。骨肉至亲,血脉相连,她是我生命的延续,更是一个全新的个体。体检抽血时,医生将橡皮筋勒到了她的臂上,左敲右打,然后将细细的针刺入了她的皮肤。那一刻,她没有哭,但我的心却痛得在滴血。
我们本是一体,但是时光在渐渐将我们剥离。初上幼儿园那几天,她哭着不愿离开我的怀抱,她漠视一切,千万人中,仿若唯独只能看得见我。她总是拉着我的手不肯放开,总是大喊着不许妈妈走。
而今,只有一个星期的功夫,她已然变成一个合格的幼儿园小朋友了。虽说还总是嘱我早早接她,但回到家中,她的嘴里不由哼出了在幼儿园新学的儿歌。话语中口口声声有了小朋友和老师的名字。
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欣慰。我的孩子,我的武文潇。我怎么可以忘记,你自己也有一双翅膀,我该冷静地,小心地把手放开,让你翱翔蓝天,享受碧海晴空的自由,领略缤纷人世的旖旎。无论疏影暗香抑或风霜雨雪,愿你挥动翅膀永不停歇,快乐,勇敢飞向你的理想!
亲亲我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