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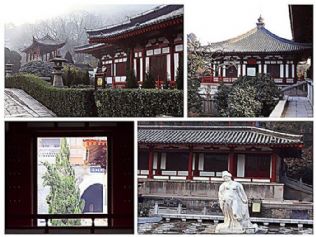
五月,徜徉千年古都的街头,在街角雾气腾腾的小店里,吃一碗羊肉泡馍,浅呷一杯薄酒,阳光淡淡,暖意融融。长街像是展开的画卷,古色古香,四平八稳的旧式建筑,瓷砖玻璃,光色迷离的商家店铺。没有荒凉,却能感觉到光阴荏苒的痕迹,在古今交汇里的沧海桑田,没有寂寥,却能感觉到历史时空的空旷冷落,默默中阅尽繁华,无喜、无悲、无聊、无奈地俯瞰这芸芸众生。
黄土高原上的槐序时节,像极了四季年华中青春的剪影,浮躁轻狂,朝云暮雨。虽然不过是几张敝帚自珍随风飘扬的破纸片,一行无人在意、渺茫难辨的足迹。但站在自我的坐标中,哪能脱得了夜郎自大的狂妄、蜗角之争的冲动。
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不过是一夜之间,从一个年龄到另一个年龄,却需要更多虚无或充实的铺垫,虽然并不明了这些究竟是财富还是负累,但我们还是要在有意或无意中找寻和丢失。吃罢了特色小吃,摸摸口袋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迈步走向城市的深处,形形色色的人群和来来往往的车辆与家乡并没有什么不同,此起彼伏的天南地北各种方言,甚至让远行的人有一种错觉,似乎只是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睡了个觉,转了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懵懂的人在哪儿都是陌生的。
避开熟悉的繁华喧闹,不知不觉走到了城墙边,沿着古老的城墙疾步而行,走了许久,也看不到城墙的尽头。天色已全然黑了下来,街灯依次亮起,饭后休闲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出现,慵懒地消费着自己的闲适时光。
街角一家服饰店门口,一个抱着孩子的男子颓然坐在地上,前面摆着一块纸片。走近前一看,却是“钱包被盗,求好心人施舍七元买票回家”的字样,下面还有一个不熟悉的地名。这男子大约三十岁的年纪,怀里四五岁的孩子已经沉沉睡着,有些污浊的小脸儿伏在男子的臂弯里,一动不动。说不清是什么吸引了我,或许是周围走来走去视而不见的人们,或许是这男子埋在灯影里、紧紧蹙着的眉头,或许是孩子恬静的睡态。我不禁停下来,在不远处端详着这父子俩。
男子穿着的白衬衫尚还洁净,裤子却有些脏了,大概是在地上坐久了。孩子的脸儿红扑扑的,给一件红色的夹克包裹着,睡得正香,忽地,小嘴巴砸吧几下,似乎做了噩梦,手脚挣扎着想要醒来,男子小心翼翼地避开刺眼的灯光,把孩子更贴近自己一些,一手在孩子身上轻轻地拍打抚摸着,孩子扭了扭身,继续睡去。偶尔有人在父子俩面前驻足,没有问询,只是目光在那纸片上转转,便很快走开。
摸摸口袋里的钞票,数了七块钱,又觉得不妥,拿出一张十块的,走过去放在男子怀里。男子惊讶地抬起头来,慌忙要站起来,却是心急,踉跄着差点摔倒。待站定了,怔怔地看着我,脸上没有喜悦,似乎是有些紧张和惊讶,喉结上下动了几下,却说不出话来。两个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忽然感觉有些尴尬,转身快步走开。听见那男子在后面嚷了句什么,未来得及细听,人已经远了。继续沿着城墙漫步,心里不禁回想起年迈的爷爷和奶奶,还有村里那个邋遢不堪四肢健全的壮年乞丐,缺吃少穿、却很少见他忍饥挨饿。记忆里,他经常在姑姑和伯父们鄙夷的目光里,蹲在奶奶的厨房里舀一大碗热腾腾的高粱面擦尖尖,吃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那时候的马路没现在这么宽阔,汽车还没有现在这么多,街道也没有这么繁华……
走了许久,夜深了,该找个旅馆休息一下了。摸了又摸裤兜里带着体温的钞票,还是有点舍不得,买了两份报纸,找个街心公园的长椅,舒舒服服躺下来,将报纸盖在身上,看看天上闪烁的星辰,迷迷糊糊坠入黄粱。身上柔和轻风抚体,耳边窸窣虫声伴梦,是睡着了的旅程,还是醒着的梦境,能清楚地听到城市进入沉睡的呼吸,能无微不至地触摸到这个城市渐渐清冷的体温。
冥冥中,一个声音缓缓地诘问着,“这是不是你期待的旅程,有漫漫风尘拂干劳累的汗水,有不期而至的偶遇,还有能唤醒内心的触动;这算不算你要的成长,真实地触及现实世界的隔膜,体验社会的温度,在人地生疏的异乡测量性格的容量,在审视回忆中,连接和阅读长辈们传递给我原本模糊的价值,用自己的语言去诠释他们想要给我的表达。”
清晨,在刷刷的扫地声中醒来,口水流了满脸,眼角沾满了空气里的浮尘,手脚冰凉,肢体酸软,意外的萎靡不振。迷迷糊糊踏上归途,在人潮汹涌的候车室里,在摩肩接踵的车厢里,如坠入软绵绵、雾蒙蒙不真实的梦幻中,除了不可遏制的响亮喷嚏提醒着身体的存在,几乎要忘记了身在何处。
一路昏昏沉沉,半坐半卧,座位从走道旁逐次移到窗边,窗外不停变化着的丰富景色,却给人一种难得的恬静。我斜倚着窗,脑海里渐渐清明,“格物致知、明心见性”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境界,现实就在自己身边,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像疲弱的身体和响亮的喷嚏一样真实,一样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