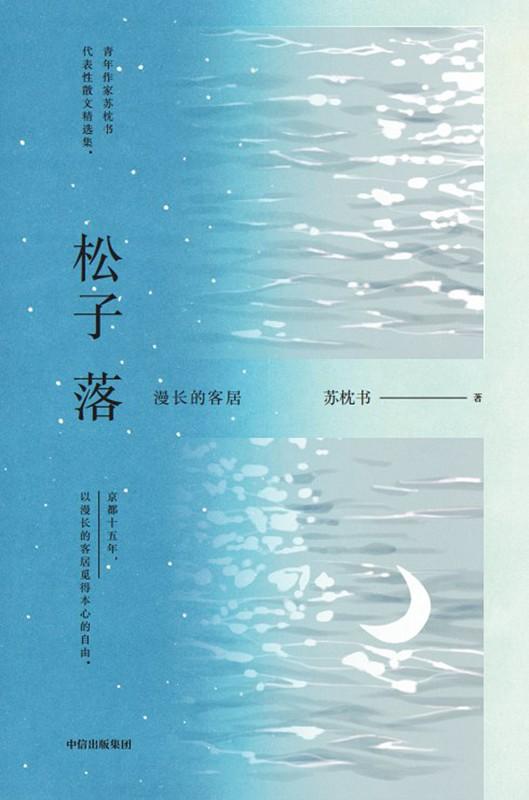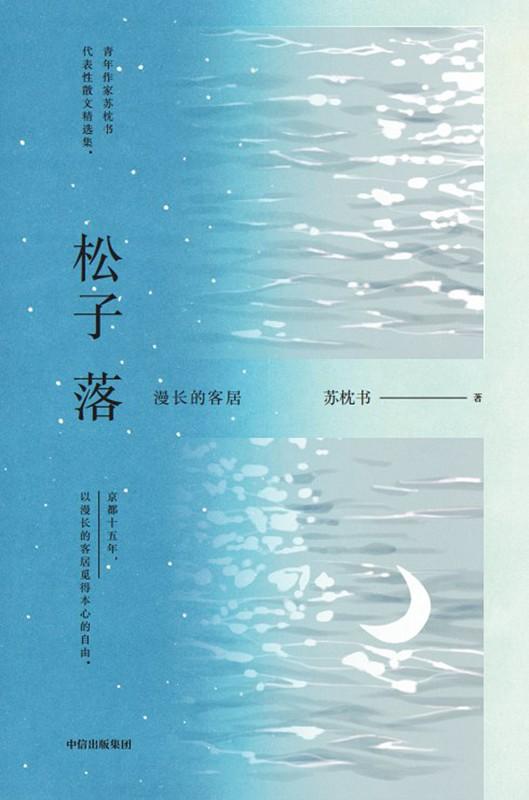
图片1
吴从周
枕书的《松子落》初版面世后,编辑老师说,想拍一段猫和松树的视频作宣传。那时枕书在京都,两只猫和我住在北京,如此两地多年。北京公园里虽然多有松树,且不少古木,但猫不愿意出门。于是最终买了一大捧松枝插瓶,摆在阳台。室内长大的猫们很觉新奇,翕着鼻子,围绕了许多圈,一直到困倦,各自在边上瞌睡起来。
不知不觉已是六年前的事。年份几个数字,说起来仿佛还是昨天。这时间不长不短,新闻变作旧闻,又还没有足够久远成为历史,只是陈旧而已。即是如此,也绝无法想象从那之后几年之间,世界竟有许多动荡降临,许多期待落空,也不能料想人生中各种阔别与永诀。回头看时,除了隔世之叹,竟然一时也找不到更确切的形容。
因为是隔几年的重版,副题“京都九年”要改成“京都十五年”。枕书对旧稿做了增删,并添了若干新篇。一则是旧版中写过的一些人和事,对之后有所交代;二则借重版之机,也对自己做了一番重审,尤其是当年面对的犹疑、困惑。人随年岁流转而移步换景,登高见远,回顾往事,或许时能发觉过去的所思所感不如此刻更加明白。现在看过去是如此,将来再看此时,想必也还是一样。倘若总是前后一致,倒不是什么好事。这些新版的变化,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不宜由我啰嗦太多。
时至今日,我也在京都住了快两年,有机会目睹枕书书中写过的种种风景与四季流转。真如堂、百万遍、寺町通、鸭川,一一变成脑海中真切的印象,闭眼也能走到。而我的日常活动范围也超过了枕书,甚至时不时能讲一些她觉得新鲜的本地见闻。也见了其中许多人,承蒙枕书多年在此间结下的友谊,令我多受善意和优待。“顺菜”餐馆的老板娘顺子阿姨听说我搬家过来,拉着我们的手直说“太好了”,又问我们吃不吃南瓜,从厨房抱出滚圆的一只来送。邻居大爷热爱海钓,问我们是否在家做饭,中国料理如何做鱼。之后某日,忽然提着两条收拾干净的大鱼敲门,说太太正因为鱼太多而生气,拿手指在头上拟魔鬼的角,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省吾一家也常来做客,每次海外旅行或是回老家,都不忘捎来手信。这些人与人的联结,让我久违地有了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感觉。
书里说,居所附近是“遍植松、柏、橡、杉、樟的山中”,因此《松子落》之题非虚。京都确实多松树。西山的善峰寺有号称日本第一的“游龙松”,树龄六百岁,横卧三十七米。不过比起来,总觉得还是北京园林的古松更苍健,且符合自然的审美。与北京的不同是,除去园林名木,这里的松树与市民生活似乎更接近一些。看起来颇有年月的院子里,往往有一棵姿态高古的松树从墙头旁逸斜出。新年之时,人家门口也多有松枝装饰,或是连根的松树幼苗,叫作“根引松”;或是配合竹子的松枝,叫作“门松”。从前只道中国人看松树,看到的是长寿、恒久、经霜而不凋,此地因袭,也取它的好寓意。这两年学了一些日文,才知道日文的松读作matsu,恰与等待(待つ)同音,因此正合新年。等待运气也好,等待新春也好,总之带着一种朝向将来的期待。而松树在英文是pine,因别离而悲伤也写作pine,词源不同,却巧合地同字。恒久、离别与等待,这几样跨文化的联想与意义交织,与“山空松子落,幽人应未眠”的古人心境,竟隔着大洋大海,殊途同归地合于一致了。
回到开头提过的两只猫,其中一只年轻的,不久突然生病离开。后来我们又收养了一只,叫金泽,枕书说取自“金泽文库”。后来,金泽与年迈的老猫白小姐一起跟我渡海,如今想必早就习惯了异国生活。枕书从前总是感叹,什么时候才能和猫真正朝夕相处?庆幸她已实现了愿望。这次新版,她命我作序,美其名曰“节约人力成本”。朋友笑我是“作序专家”,我觉得是自己的幸运。枕书说京都十五年,而我和她相处的年份差不多也是这么久,对人生而言实在不算短。我期待读到她更多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