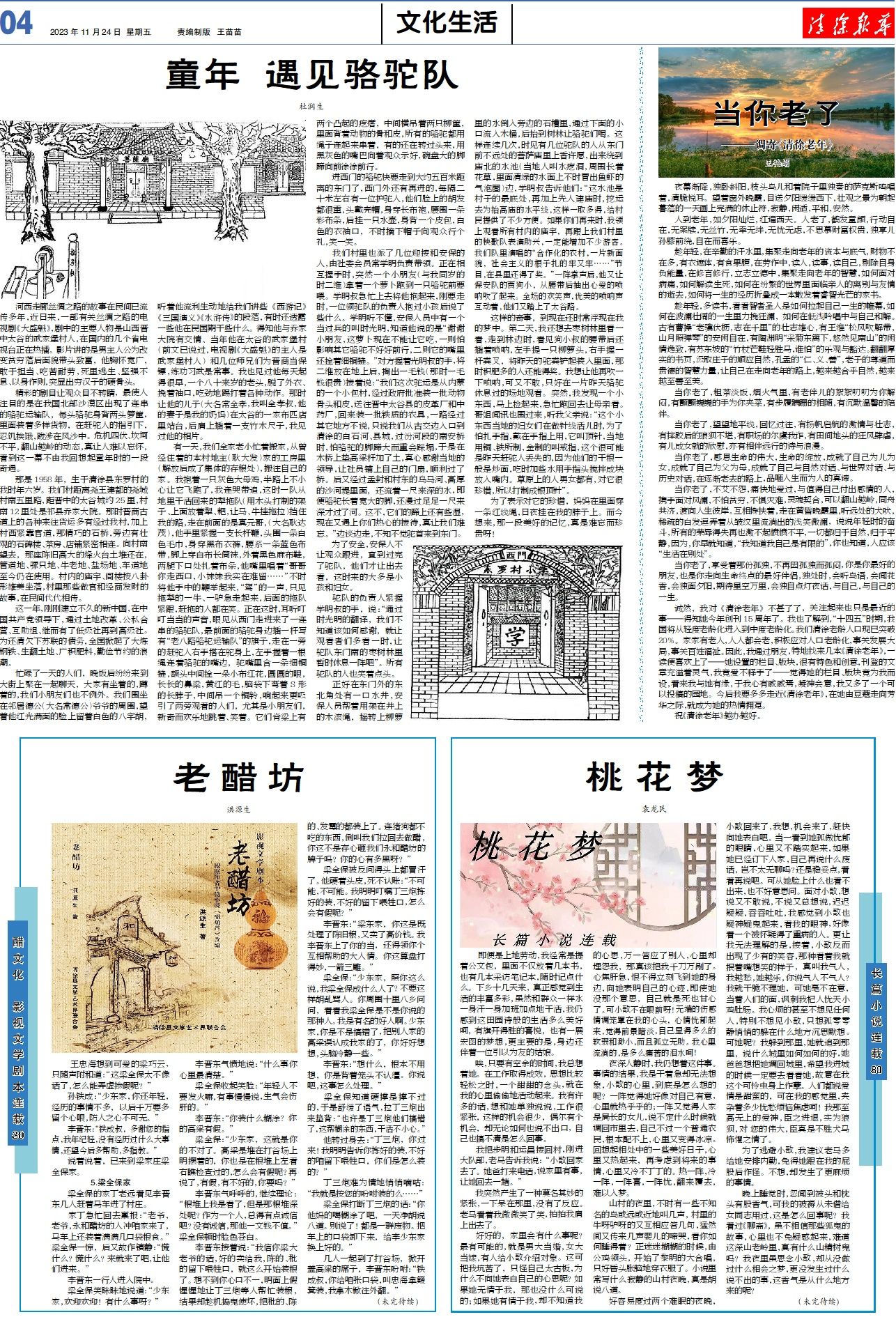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故事在民间已流传多年,近日来,一部有关丝绸之路的电视剧《大盛魁》,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山西晋中太谷的武家堡村人,在国内的几个省电视台正在热播。影片讲的是男主人公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带头致富,他胸怀宽广,敢于担当、吃苦耐劳,死里逃生、坚强不息、以身作则,突显出穷汉子的硬骨头。
精彩的剧目让观众目不转睛,最使人注目的是在我国北部沙漠区出现了连串的骆驼运输队,每头骆驼身背两头箩筐,里面装着多样货物,在赶驼人的指引下,忍饥挨饿,跋涉在风沙中。危机四伏、坎坷不平,翻山越岭的动态,真让人难以忘怀,看到这一幕不由我回想起童年时的一段奇遇。
那是1958年,生于清徐县东罗村的我时年六岁。我们村距离尧王建都的尧城村南五里路,距晋中的太谷城约25里,村南12里处是祁县乔家大院。那时晋商古道上的各种来往货运多有经过我村,加上村西紧靠官道,那精巧的石桥,旁边有壮观的石碑楼、茶房、店铺紧密相连。向村南望去,那座陈旧高大的烽火台土堆还在,管道地、骡只地、牛老地、盐场地、车道地至今仍在使用。村内的庙宇、阁楼按八卦形雄美坐落,村里那些做官和经商发财的故事,在民间代代相传。
这一年,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公私合营、互助组、继而有了低级社再到高级社。为还清欠下苏联的债务,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生翻土地、广积肥料,勤俭节约的浪潮。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晚饭后纷纷来到大街上聚在一起聊天,大家有坐着的,蹲着的,我们小朋友们也不例外。我们围坐在邻居德公(大名常德公)爷爷的周围,望着他红光满面的脸上留着白色的八字胡,听着他流利生动地给我们讲些《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段落,有时还透露一些他在民国期干些什么。得知他与乔家大院有交情、当年他在太谷的武家堡村(前文已说过,电视剧《大盛魁》的主人是武家堡村人)和几位师兄们为晋商当保镖,练功习武是常事。我也见过他每天起得很早,一个八十来岁的老头,脱了外衣、挽着袖口,吃劲地踢打着各种动作。那时让他的儿子(大名常全孝,我叫全孝叔,他的妻子是我的奶妈)在太谷的一家布匹店里站台,后肩上插着一支竹木尺子,我见过他的相片。
有一天,我们全家老小忙着搬家,从曾经住着的本村地主(耿大发)家的工房里(解放后成了集体的存粮处),搬往自己的家。我抱着一只灰色大母鸡,半路上不小心让它飞跑了,我连哭带追,这时一队从地里干活回来的犁拖队(用木头打制的架子、上面放着犁、耙,让马、牛挂拖拉)挡住我的路,走在前面的是真元哥,(大名耿达茂),他手里紧握一支长杆鞭,头围一条白色毛巾,身穿黑布衣裤,腰系一条蓝色布带,脚上穿白布长筒袜,外着黑色麻布鞋,两腿下口处扎着布条,他嘴里唱着“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不时将他手中的鞭举起来,“驾”的一声,只见拖犁的一牛、一驴急走起来,后面的拖队紧跟,赶拖的人都在笑。正在这时,耳听叮叮当当的声音,眼见从西门走进来了一连串的骆驼队,最前面的骆驼身边插一杆写有“老八路骆驼运输队”的旗子,走在一旁的赶驼人右手搭在驼身上,左手握着一根绳连着骆驼的嘴边,驼嘴里含一条细铜链,额头中间拴一朵小布红花,圆圆的眼,长长的鼻梁,黄红的毛,脑袋下弯着S形的长脖子,中间吊一个铜铃,响起来更吸引了两旁观看的人们,尤其是小朋友们,新奇而欢乐地跳着、笑着。它们脊梁上有两个凸起的疙瘩,中间横吊着两只柳筐,里面背着动物的骨和皮,所有的骆驼都用绳子连起来串着,有的还在转过头来,用黑灰色的嘴巴向着观众示好,碗盘大的脚蹄向前徐徐前行。
进西门的骆驼快要走到大约五百米距离的东门了,西门外还有再进的,每隔二十米左右有一位护驼人,他们脸上的胡发都很重,头戴壳帽,身穿长布袍,腰围一条彩布条,后挂一只水壶,身背一个皮包,白色的衣袖口,不时摘下帽子向观众行个礼,笑一笑。
我们村里也派了几位迎接和安保的人,由社委会员常学明负责带领。正在相互握手时,突然一个小朋友(与我同岁的时二维)拿着一个萝卜跑到一只骆驼前要喂。学明叔急忙上去将他抱起来,刚要走时,一位领驼队的负责人抱过小孩后说了些什么。学明听不懂,安保人员中有一个当过兵的叫时光明,知道他说的是“谢谢小朋友,这萝卜现在不能让它吃,一则怕影响其它骆驼不好好前行,二则它的嘴里还拴着细铜链。”对方握着光明叔的手,将二维放在地上后,掏出一毛钱(那时一毛钱很贵)接着说:“我们这次驼运是从内蒙的一个小包村,经过政府批准装一批动物骨头和皮,送往晋中太谷县的皮革厂和中药厂,回来装一批铁质的农具,一路经过其它地方不说,只说我们从古交边入口到清徐的白石河、县城,过汾河段的南安桥时,怕骆驼的脚蹄大而重会踩塌,于是在木桥上垫高粱杆加了土,真心感谢当地的领导,让社员铺上自己的门扇,顺利过了桥。后又经过孟封和村东的乌马河、高厚的沙河堤里面,还流着一尺来深的水,即便骆驼长着宽大的脚,还漫过足足一尺来深才过了河。这不,它们的蹄上还有些湿,现在又遇上你们热心的接待,真让我们难忘。”边谈边走,不知不觉驼首来到东门。
为了安全,安保人不让观众跟进,直到过完了驼队,他们才让出去看,这时来的大多是小孩和妇女。
驼队的负责人紧握学明叔的手,说:“通过时光明的翻译,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感谢,就让观看者们多看一时,让驼队东门南的枣树林里暂时休息一阵吧”。所有驼队的人也笑着点头。
正好在东门外的东北角处有一口水井,安保人员帮着用架在井上的木滚绳,摇转上柳箩里的水倒入旁边的石槽里,通过下面的小口流入木桶,后抬到树林让骆驼们喝。这样连续几次,时见有几位驼队的人从东门前不远处的菩萨庙里上香许愿,出来绕到庙北的水池(当地人叫水疙洞,周围长着花草,里面清绿的水面上不时冒出鱼虾的气泡圈)边,学明叔告诉他们:“这水池是村子的最底处,再加上先人建庙时,挖运去为抬高庙的水平线,这样一取多得,给村民提供了不少方便。如果你们再来时,我领上观看所有村内的庙宇,再跟上我们村里的秧歌队表演助兴,一定能增加不少游客。我们队里演唱的“合作化的农村,一片新面貌,社会主义的根子扎的牢又牢……”节目,在县里还得了奖。”一阵掌声后,他又让保安队的贾狗小,从腰带后抽出心爱的唢呐吹了起来。全场的欢笑声,优美的唢呐声互动着,他们又踏上了太谷路。
这样的奇事,到现在还时常浮现在我的梦中。第二天,我还想去枣树林里看一看,走到林边时,看见狗小叔的腰带后还插着唢呐,左手提一只柳箩头,右手握一杆粪叉,将昨天的驼粪铲起装入里面,那时积肥多的人还能得奖。我想让他再吹一下唢呐,可又不敢,只好在一片昨天骆驼休息过的场地观看。突然,我发现一个小东西,马上捡起来,急忙跑回去让母亲看。哥姐闻讯也围过来,听我父亲说:“这个小东西当地的妇女们在做针线活儿时,为了怕扎手指,戴在手指上用,它叫顶针,当地用铜、铁所制,金制的叫戒指,这个很可能是昨天赶驼人丢失的,因为他们的干粮一般是炒面,吃时加些水用手指头搅拌成块放入嘴内。草原上的人男女都有,对它很珍惜,所以打制成银顶针”。
为了表示对它的珍惜,妈妈在里面穿一条红线绳,日夜挂在我的脖子上。而今想来,那一段美好的记忆,真是难忘而珍贵呀!
童年遇见骆驼队
杜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