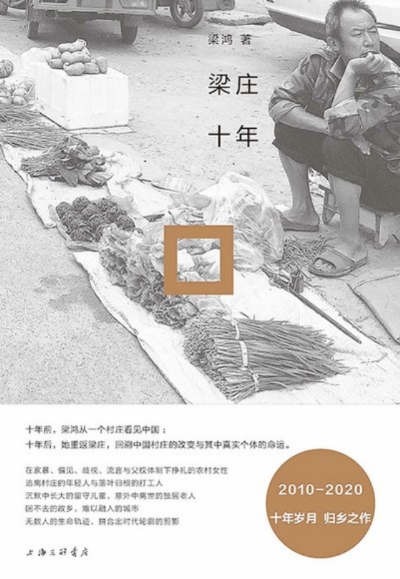万物在深秋静静贮存,迎接漫长的冬天。
《梁庄十年》,我们会发现,在一种城市人的眼光中,他的生活当然已经彻底的失败,但在梁庄,这一切还远未见分晓。
新书记栓子还在勉力试图用技术的力量为生命所用,如同梁鸿的描写,他雄心勃勃地要以“梁庄人”的名一改村中的破败和陋习,但这一切当然阻隔重重,不仅是他自己在外面的生意和他在梁庄的牵挂的冲突,还有这种技术与生命的角力。这是一出现代的悲剧,拴子心中的伟业绝不会顺利,等待他的一定是不理解、背叛与希望的一再兴起和失落。
不过好在大地永在。
大地到底有什么力量呢?让二十多岁的梁安,这个草莽年轻人在北京顺义装修着新富阶层的豪宅,一年已有四五十万收入,这是让很多城市人都望尘莫及的能力,他在这个技术编织的都市中游刃有余,已经经过了起伏的考验。城市当然也赋予了他更上层楼的野望,但土地依然让他在如此小的年纪便拖家带口地回到梁庄。在城市他同样患上名为“抑郁症”的现代病,这不过是我们所有人在技术中的无根性。但在他的母亲看来,这是一种“中邪”,梁安回到梁庄后的痊愈,是她切切为他驱鬼祈福的结果,这不是一个荒唐的解释。根植于大地中的人际情感,驱散着城市野心与算计对人的吞噬,以神魔交战来看待这场人的生活与心灵的角逐并没什么不妥。
在我与梁安交谈的时候,我的脑里一次都没有浮现对他事业放弃的“可惜”,而是“羡慕”,梁庄人尚有乡村可以退守,我们呢?
老人们在村庄中兀自死去,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接触现代医学,在诊断、症状的解释,药品那令人费解的化学名称中度过晚年,并费力在这些技术构造的如机器般精确的理论中感受自己的痛苦。但即便如此,更多人依然以天命和道德理解着这些痛苦,如同衰败的庄稼与涨落的大河。生死是道义,而非原子组成分子的运动。人们在道义中激烈地捍卫着尊严与情感,并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终局。在这里,基因与脑机接口所带来的永生期盼会被视作毫无必要和完全不可理喻的想象,那会像是对生命基本常识缺乏而产生的疯癫,比清立那因为尊严逼迫而产生的疯癫荒谬一万倍。
我还难以忘记一双手,他兴致勃勃地为我指点义生家那栋令城市人都艳羡的豪宅,但他讲解的话语渐渐模糊,义生的豪宅也不过是城市景观对乡村的简单侵入,不过是有人将顺义的一栋别墅发射到了这里。我难以不去注意那双手,他的手背黝黑,粗糙干裂,但手掌一面却是奇异的淡黄色,那明显来自经年累月某种化学物质的烘烤和摧残,为我默默讲述他那悲惨的过往。他的手伤痕累累,很多指节包着已经肮脏的绷带。这是一双受过多少苦难的手,但在那极不自然的淡黄色之下,我仍然能感到血气的蔓延,从粗粝的老茧中泛出的某种韧性和生机。因为你从他的面庞和神情中丝毫已经看不到这双手的痛苦,土地已经将某种技术的荒唐纳入其中,那被破坏的,得到了接纳和谅解。
那只是短暂的两天,却因为梁鸿前后的书写令我震撼,并在这本《梁庄十年》中不断将我拉回那个风清气朗的日子,我目睹衰败与痛苦,目睹技术的侵入与不甘,目睹抵抗和疲惫。但究竟我目睹着美丽,那压迫着我泪腺的不是悲剧,而是美丽,我们在城市的精致与奇观中遥不可及的美丽。原野,草地,高树成行,万物坚韧持存,连同一切人的生命和痛苦,在名为梁庄的天地中如湍河静静流淌。水涨水落,被污染了,又在流淌中慢慢洁净着,被伤害夺取的,又在深深渊源那隐秘的生机中慢慢愈合着。那是令人思念与羡慕的美丽,让我无数次在都市中茫然四顾,不见那些原野和河流。
我多么想念梁庄,想念大姐、二姐和梁鸿一家人,想念霞子姐,想念清道和他的园子,想念梁安和他那倔强而满不在乎的神情,想念五奶奶,想念那些野性又极端害羞的孩子们,想念那双大手和他的主人。我多么想念梁庄,希望他们被土地永恒地庇佑。
苍天在上,愿你聆听世间的哭喊。
大河在下,愿你带走我们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