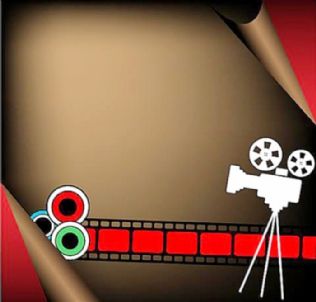“沉浸浓郁、含英嚼华”这八个字,是1959年我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期间老书法家周昔非(已故)为我的题词。这八个字是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在题为《进学解》中夸赞才学如汉代司马相如者的,我何能当之,只是我性格比较内向,又苟言笑而已。倒也可以理解为我当沉浸在电影艺术浓郁的氛围中,探求其中精华,也还说得过去。
1958年秋末冬初,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山西省上马电影制片厂,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塞周牵头,组织人事科负责人李芳、段成明等,在太原市鼓楼街八号院挂牌成立“山西省电影制片厂”又吸收省文化部门年轻有为的几名同志负责招收职工。发出广告后不久,即招收近三十名符合条件的大中学生投入电影事业。十一月初,即乘火车赴吉林长春电影制片厂学习。至今已有六十余年,还记得几个清徐籍人,一位是南关大街郭庆发的三儿子郭福海,他从太中高中毕业,善打篮球,他到长影后与我在特技车间学习电影字幕摄影,学完后改了行,却在省电影公司退休。成晋业是西青堆人,六中毕业后考入太原轻工业学院,因对专业不感兴趣,退学入电影厂,学习场记、编导。还有一位是孟封闫家营的郑春雨,他擅长音乐,吹拉弹唱都有两下,他在长影学习后,转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终生搞录音,在北影退休后,还被返聘工作多年。
我是最不屑的一个。在长影学的电影字幕书写。说白了就是写字。但写字也不简单。要学会写各种字体的字,无论写片头大字还是其中小字,字体都要跟电影内容情节相配合,要根据影片情节写出适当的字体。这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还要设计片头背景。总之,那也是一种须要认真学习的专门学问。然而,我们每天学习还算轻松,没具体任务,也不考核。看电影、评片子,只要会说看后感就行。也不一定看后都评,没时间了,就只看不评。主要是跟着电影厂各个车间、部门的老前辈们学习实际操作,有学表演的、有学编导的、有学摄影的,这些都是较有才华的学员。
那段时间,山西电影厂与长影合作摄制了好几部著名电影。最著名的有马烽编写的,以山西汾阳贾家庄为背景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男主角高文武女主角孔淑贞,至今印象深刻。该电影对当代青年返乡务农建设美好家乡,发挥了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此外,还有赵树理的作品改编的《三里湾》《三年早知道》等。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每人每月只有二十多斤粮,副食奇缺,主食主要是红红的高粱米,或稀粥、或干饭。主要演职人员也和大家一样在大食堂吃饭。白杨、田华、郭振清、李亚林等著名演员都在大食堂的窗口排队打饭,同桌共餐,没有一点特殊待遇。有时,拍摄过于紧张,不卸妆,匆匆到食堂吃点饭就又去拍戏了。为了节省开支,学员们常去充当群众演员参加拍摄。一次拍朝鲜剧《金玉姬》缺群众演员,就把我们拉了去,穿上鬼子的军装,导演简单说了说剧情,让我们听见爆炸声就倒下。我们演了一出只有动作、不见表情、没有语言的被炸死日本鬼子的戏。
长春的天气很冷。因不适应,常患感冒。在长春时,我曾得了一次大病,吃药打针七八天,高烧不退,不见好转。医生怀疑我得了传染病,把我隔离到长影琴师的琴房里。尽管有传染病之嫌,领导和同志们却都来看我,有的还带来礼物。人人都关心我,让我感动万分,他们的情意,令我至今难以忘怀。我的病,久治不愈。最后不得不送到吉林省人民医院诊治。经多位专家会诊,确诊为麻疹,以麻疹治疗几天后,病情大为好转。出院疗养时,我又住到了练琴房。琴师郑秀珍大姐在外间练琴时,还常抽空来里屋看我、安慰我。在寒冷的东北,在我生病卧床的痛苦中,领导和同志们都来看我、安慰我,他们对我的关爱,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