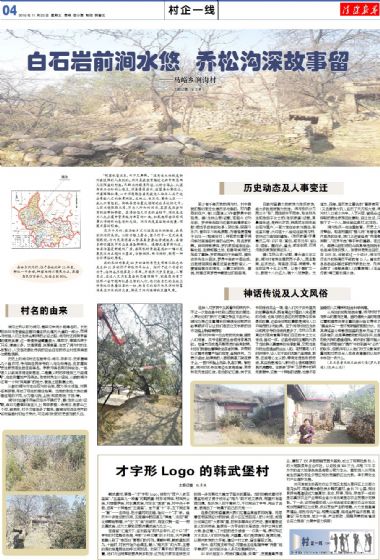马峪乡涧沟村:位于县城北部21华里,耕地一千余亩,种植结构以葡果为主,在籍
居民四百余人,张姓占到90%。“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大约就是针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的。涧沟是我经常路过也非常熟悉而又很陌生的村庄。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榆古路上、从通向白石云松的山路上,顺着潺潺溪水,遥望着如黛远山,听着阵阵松涛,心中怀想默念着无数先人和今人关于这些景致人文的华章词赋。龙林山、白石沟、葡峰山庄……我从不曾想到,掩映在清徐星光熠熠的众多地标之中,山环水绕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的涧沟,其实是这些所有的纽带和桥梁。在清徐悠久历史的坐标中,涧沟是这片人文土壤中营养极为丰富的一块。如果把那些华丽词章比作绚丽的色彩和光焰,涧沟就是其后输送能量、深藏不露的明珠。
农历十月初,经马峪乡文化站庞站长的联络,我来到涧沟村采访。从榆古路上看去,整个村子一览无余呈现眼前,村内民居顺着山势层层叠叠地修建起来,在诸多新旧建筑中间丛生着各种树木,通衢大道穿村而过,白石沟里是新建的厂房,在深秋的景致里宛如一幅以发展变迁为主题的水墨画。动静相依、新旧相对,颇有一种古朴守拙的质感。
我的采访对象是68岁的该村原党支部书记张志林先生和51岁的村干部张丽平女士,相对于这个古老的村子,他俩也只能算是小字辈。历朝历代岁月更迭,人事变迁,在这人文历史复杂的交错演绎中,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可敬而认真生活的人们,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热情地记录着这里的一切,把自己的经历和见识的财富传承在不休的时光里,构成了涧沟独特的底蕴气质。
村名的由来
涧沟之所以称为涧沟,是因沟中涧水而得名的。长长的白石沟是曾经古晋阳通往陕北通关大道的一部分,而涧沟村是人们上龙林山朝拜的必经之路,涧沟村还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一带煤炭储藏量很大、煤质好,煤层浅便于开采,煤窑众多。交通便捷、资源丰富,注定了涧沟村的生息繁衍、人文活动要比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村庄来得更加频繁活跃。
历史上的涧沟村还包括寺沟、涧沟、李家沟、史家崖等几个自然村,寺沟因在梵宇寺的入沟处而得名,史家崖因史姓家族在此居住而得名。李家沟得名有两种说法,一是很久以前有李姓在此居住,二是集义村的李姓开三尺窑煤矿,在此购置地产而得名。张志林先生介绍说,从前的涧沟还有一个叫“鸡尾寨”的地方,曾是土匪聚集之地。
从前的涧沟村在白石沟的谷地,因为洪水泛滥,村民逐渐移居,形成了现在的居住格局。当地的张姓大族依据居住地的不同,分为楼儿院(上院)和底昂院(下院)等。
涧沟村始建于何年已经并不确切了,据《龙林山志》记载,白石沟最早只有庄儿上(即李家楼)、寺涧沟、张家山三个村,到后来,村子才逐渐多了起来。据涧沟村近在咫尺的邻村后窑村初始于宋代,可见涧沟村的历史更加的久远。
历史动态及人事变迁
至少有千年历史的涧沟村,村中居民的繁衍变迁也是历尽沧桑的。村内最早的住户,有《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祖先。据《龙林山志》记载,在距今1070年前,罗仲祥由四川成都来到清源做仆射(相当于后来的知县),到位后,因四川水灾,晋阳平川战乱频繁,为避难便落籍于白马一(现涧沟村),将祖茔也置于涧沟斜对面后窑村后的山凹中,现名罗家围。后因种种原因,罗氏家族逐渐迁出。解放后,政府规整土地,后窑与涧沟的土地做了置换,罗家围遂归于后窑村。据张志林先生介绍说,罗贯中被家中逐出后,远赴梗阳来投靠在这里做官的伯父,一度曾经居住在涧沟,从事文学创作。据说,村里还有罗贯中寄居过的旧窑洞。
目前村里最大的家族为张氏家族,绝大多数居民皆为张姓。涧沟张氏分为两三个“张”,同姓却并不同宗。张志林先生和张丽平女士的《张氏家谱》记载,其鼻祖张迪,是明代岁贡,明洪武年间来到白石沟落户,一至六世在安家沟居住,后迁至石窖,大约在十八世纪迁到涧沟村,很快成为当地的望族。《张氏家谱》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首创,咸丰元年(1851年)续修。据统计,道光、咸丰年间,仅涧沟张氏家族就有近千人。
据《龙林山志》记载,清光绪三年之前,涧沟村有常住居民两千多人,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有酒店、旅店、商铺等。每年的正月十五上元节,以每个煤矿为一伙,要闹十八伙红火,唱十八场秧歌。光绪三、四年,是历史上著名的“晋豫奇荒”(又名晋豫大饥),经历了天灾和大疫,涧沟村人口减少大半。人丁兴旺、曾经出过榜眼的史姓家族因此衰败,到上世纪,只剩下了一个人,搬迁到梁泉村,改姓陈。
涧沟张氏一向注重教育,历史上人才辈出。现在村里的“楼儿院”有曾任清代官员的住宅,院门上还曾经有“光绪年间制”、“流芳千古”等字样的匾额。在近代,阎锡山政权时的山西高等法院院长也是涧沟张氏族人。张志林老先生回忆,在1985年,他曾做过一个统计,涧沟村仅在外的科局级干部就有13人。曾在我县县委组织部任职的作家张拉发,先后出版了《金觚奇案》、《古墓惊魂》、《玉谷传奇》等三部长篇小说。
神话传说及人文风俗
在后人对罗贯中及其著作的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在其中找到山西故地的痕迹。人声纷纭的“罗氏”归属之争且不去讨论,涧沟及周边丰富精彩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们在这位文学家的创作之路上稍窥端倪吧!
涧沟村中有一处古老的狐突庙,据老人们传言,狐爷在封建社会被传非常灵验。每逢节日或是天旱雨涝的非常时期,村民们就要抬着神像出去做祈祷。祈雨的仪式程序有着严格的规定,各种讲究。为表示虔诚,抬神像的人要把铡草刀架在脖子上,一百只针拴上布条,扎在双臂。解放前,涧沟的狐爷在周边也享有盛誉,张志林老先生回忆说,在他的记忆里,关于狐爷的传说非止一端,老人们关于狐爷显灵的故事非常多,既有周边村落的人来还愿的传说,也有与附近县区的村落争夺狐爷像的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涧沟人口口相传的乡村故典。至于涧沟村附近龙林山和梵宇寺的传说就更多了,龙林山及其周边村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本土文化传说,自成一体。这些传说的主题既代表了当地群众真善美的传承教育,又和当地风物古迹结合的丝丝入扣。在村里老人们的讲诉中,让人忍不住的沉醉乃至痴迷,我想,这些唯心主义的、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其实就是涧沟人淳朴的心性和理想的自然裸露吧。在我县“罗学”及罗贯中的研究课题中,这是一个神秘的话题,也是不容回避的人文精神和社会科学问题。
从传统的地形地貌来看,涧沟村附于龙林山的潜龙之尾。古时通关大道的地理位置和煤炭资源丰富的身份给它带来了“塞翁失马”一般不知祸福的起起伏伏。而其绵延至今却愈发旺盛的生命力给了我很多启示,这是厚德载物的现实陈诉,这是物竞天择的最佳选择。或许我们都不能从那些坎坷艰难的“偶然”中找到其与“必然”的联系,但或许可以从他们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对历史与人性点点滴滴的认知中中学到一点什么。
(本文参考文献及数据引自《罗氏家谱》、《龙林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