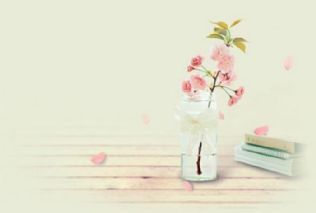11月6日,老伴回来说:郭维忠走了。我心里顿时一紧,万分悲痛怅然。前不久,在他患病期间,我去探望,恰好他女儿给他端来一碗饭菜,郭老吃得很香。我笑说:“老了,能吃饭就好。你看我,156斤,什么病都能扛住。”他听了立刻说:“我180斤呢”。那语气很是自信乐观。当时我想,郭老身体这么壮实,调养一段时日,肯定就没问题了。不料,他却走了……这怎能不让人心痛。于是,在老伴的搀扶下我去了郭老家,在灵前上了香,并对罗大姐安慰了一番。
我与郭老初次相识,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讨论街道命名的会议上,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挂职副书记韩石山。在讨论东湖大街命名时,郭老说:“应将东湖大街更名为湖东大街,东面的街道可命名为湖东二街,再往东建街道,可以叫湖东三街嘛!”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当时,我觉得这位文人说话干脆利索,简洁明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后来,在《清徐报导》上展开马鸣山之争时,他写的文章《浅议马鸣山、马名山之释》打动了我。我研究了大家的文章及有关资料后,也写了《我对马鸣山得名的看法》一文,认为马鸣山如何书写并不重要,应将马鸣山与龙林山表述清楚才是关键。事后,在县史志办召开的年会上,我提议写《龙林山志》,郭老立即表示赞成,并得到当时任副县长的裴耀军的支持。这样一来,我与郭老开始接触频繁,我们两人曾八上龙林山调查研究,回来则一起讨论写作,我打初稿,郭老修改,杀青后,我提议同署两人的名字,可郭老很谦虚,他再三斟酌后,改为“李中编著,郭维忠审订”。
再后来,政协编“文化历史丛书”,我们又一起编写《清源古城》、《清徐古寺庙》等,整天在一起讨论,一起研究,越来越熟络起来,我几乎成了他家的常客。郭老藏书甚多,如《晋祠志》、《山右丛书》等,在市场上是很难买到的,我便常常借来阅读,并参考写作,受益匪浅。郭老博学多才,每说一件事,都有头有尾,十分细腻生动,并有独特见解。与他聊天,如同看戏曲,如同饮村醪,却又比看书、看戏还过瘾。真是听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可以说,郭老是我的恩师,是我的挚友,同他相处了十多年,却觉得好像处了一辈子。再加上我俩脾气相投,爱好相同,觉得两人比亲兄弟还亲。因此,惊闻他的仙逝,我心中好像被掏空了一般,久久不能平静。真是:
乍听噩耗魂梦惊,怆然泪下失师朋。
你我天人两相隔,再有难题该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