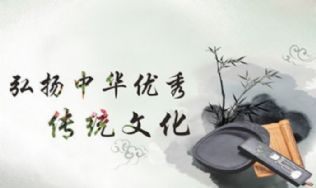做人处事要忠诚,这一观念已经根植到国人的日常思维之中,成为古往今来时刻高悬在国人心头之上的道德律令。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柱石,从远古的诗歌里传唱,到孔夫子复兴儒家思想之时把它发扬光大,再到现在君亡的时代依旧被惦念着,可以说历经五千余年。这其中不单有君权存续的五千余年,也有民主新生的一百多年。
忠,忠诚、忠恕、忠贞、尽忠职守。现代《新华词典》(1988年修订版,1989年9月第2版,第1165页)的释义是:赤诚,尽心竭力。单从字面上的理解,忠字本身并没有明示的对象指向以及客体范围,它只是对内心或者行为的一种状态要求。如果单是如此,它也不成为文化。忠文化的成形必须有系统的思想理论,包括对“忠于谁”的对象和“忠于什么”的客体作出明确回答,以及对如何忠又如何不忠等问题作出界定。
早前的忠文化大概也有多种版本吧,但时至今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流行的唯有儒家的忠文化。由此,解读传统忠文化就不能不拿儒家版本作参照。尽管儒家版本的忠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但核心的东西大抵相同。那么,儒家版本的忠文化是怎么构建的呢?
“上思利民,忠也”,“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教人以善谓之忠”,“尽已谓忠”,“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还有不敬、不满、微词或诽谤君主的皆为不忠的做法,还有忠臣不事二主的做人处事格言,还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忠臣样板。
儒家忠文化主要调整臣民对君主(包括封建王朝即国家)的关系,也就确定了忠的对象主要是君主,忠的主体主要是臣民。在实践中忠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却更加宽泛,比如其对象延伸到雇主、先主、上司、事主等等,其主体也相应延伸到各种对象的相对一方。以现代法律关系的视角来分析,在整体上忠文化的实质是与人身相关的一种社会关系,但这种社会关系侧重于君主与臣民之间,其与人身的关联程度仅次于家庭关系。忠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用形象的话语来概括就是主仆关系。
那么,儒家忠文化对忠的内容有什么要求呢?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利益维护,二是服从旨意,三是尽心竭力。明确了忠的内容,不忠的表现就可想而知:一是损害利益,二是背叛旨意,三是敷衍应付。而且,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被要求以无偿和无条件的付出,即不存在对价补偿或者其他的交易方式,可以说是纯义务性。这些内容不单是思想上的要求,还包括行为。因此,忠文化的仆从对主人具有深重的依附关系,而且是一种人身的依附关系。
在理论上忠文化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有前提条件的,一旦逾越这一前提条件,作为仆从便可以割断或者脱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这个前提条件是指主人的作为或者利益诉求必须符合天道,通俗地说就是要有正义性。关于这一点荀子就提出了“从道不从君”观点;从孟子对周王伐纣事件的解释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他否认周王存在弑君的不忠行为,理由是纣王已然成了独夫,即为天道所遗弃了,便不再是君,如何弑“君”了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唯有君主才有资格代表上天,这无关君主身份和地位的取得方式,比如禅让、继承、政变或者造反等方式均可;同样无关君主个人的品行、嗜好、作风以及智力状况,比如贪婪、好色、嗜杀、痴呆、癫狂等等皆无不可。这就是可怕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其结果导致君主意志替代了天道,这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对天道的毁弃。
缘此,在实践中不忠的前提条件形同虚设,何况君主享有最终的话语权。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常见一种说法,就是主人对仆从忠心程度的要求竟拿狗做比,不过也确有自比为狗以表忠心的仆从。
原本天道是恒常不变的正义,存在天地之间,并超越世间万物。而君主意志呢?它只是一个一己之私的变化无常的人身欲求和意愿,无所谓仁爱、聪慧或者贤德,与正义无涉。儒家思想将君主身份与天道建立固定关联,甚至划上等号,就使天道变得可以人为地窃取、抢夺或者强占。因为最终是以成王败寇的方式来确定与否符合天道,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因此,可以不忠的前提条件实质上不是什么天道,而是霸道即强者的道,实际上天道服务于霸道。比如不忠反而还有一个美名,即识时务者;那么,不识时务呢?就是不知顺从天道,倒成了愚忠。现实中的时务却不易识的,因为这需要准确地预见将来的成败,要是不能最终站在胜利者一边,结局也不免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当然,孔孟对君主也提出了对待臣民的要求,比如要懂得体恤、要有礼节,要视如手足腹心等等。在主仆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这种要求其实是空头的,因为历史上压根就没有因为君主不体恤造反而不被视为谋反或者叛乱的事例。
从上述层面上理解,儒家文化实践教化的结果却是去仁义而兴权谋,所以历史上满满的是假仁假义者、乱臣贼子和无道暴君。不可否认,忠文化对稳固君权具有很大的用处,这不过是强化了君主专制统治的地位。它最终抵挡不住私欲的冲击,反而成了造就社会苦难的祸首。依我之见,现在很多“团结”“紧密团结”的话语便有传统忠文化的意味。如果团结不但要求思想一统,还要求行动一统,并且质疑不得反对不得,这其中就具备明显的人身依附属性了。
通过对传统忠文化的分析可知,忠文化的社会实践效果只是集中和强大了某种社会力量。不否认在理论上忠文化包含对正义和良善的诉求,但由于维护主人利益和服从主人旨意被摆到主仆关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其力量集结的过程是通过仆从对自我利益的放弃和对正义追求的让步来实现。因此,忠文化实践的最终结局反而是对天道正义的自我毁弃,其对正义和良善的看护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虚无飘渺。
基于忠文化的人身依附属性,所以说它有利于稳固君权,同时这也决定了其本身缺失对君权进行必要制约或者抗衡的力量。集结之后的力量最后听凭君主意志的号令,偏离人类对正义和良善追求的目的;也造成社会力量的失衡,为专制和人治创造条件。传统忠文化在促成力量集结之后缺乏对力量进行合理的指向,这是传统忠文化最根本的弊病所在,使它最终丧失了对人类进步与文明的指导意义。
那么,传统忠文化是否一文不值呢?是否应当彻底遗弃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它可通过修正的方式得到新生,也是一种值得继承的文化。人很难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认知的真确性更多地建立在先前和如今我们可以在实践中观察的经验之上,认知本身是一个不断趋向真确的过程。相信并坚持儒家先贤们找到了放之未来还皆准的法则,这是后人无知的过错和不思进取的惰性,无关儒家思想之于当时的伟大以及重要意义。
人类的文明始于对社会秩序的认知和建构,这是人类开始自主自身命运的标志。我在解析人性的一些文章中提到,人性实质是根植于人身内在的需求和意愿,它是每一个体人普遍具有和共通的东西,并且具有显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就是说,只要人身存在,人总要通过自身行为去获取需求和意愿的满足。在这显现过程中个体人行为的方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具有逃避劳动和趋向愉悦的倾向。任由个体作出符合自身需求和意愿的行为,最终必定要损害其他个体以及整体的生存和发展。
散乱和无序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大敌,而秩序的形成需要力量的支撑,人类在自然界中谋求生存发展也需要强健自身的力量。例如坚贞、刚劲、勇敢、尽心竭力等品性或者品格一直都是人类所倡导的,这都源于强健力量的需要。传统忠文化在强健力量方面是大有用处的,符合人类自身的理性要求,而新生的关键就在于应当重新赋予力量的指向。
以忠字为例,从造字的构造上说它具有“内心秉持中正”的涵义,从笔画的形象上说中间竖划长直而有力,亦有贯穿始终和刚劲的意味。古汉字的造字颇为奇异,但造字过程的文字释义不能成为证明字义文化合理性的依据,作为一种援引倒也无妨。
秉持中正和守护正义应然是忠文化的首要内涵,可以确定为忠的指向,由此将解除人身依附关系的属性。此外,忠文化还得继承坚贞和尽心竭力的品性或者品格要求,这是实践忠文化秉持中正和守护正义之要义的力量体现,是为其要义实现提供的必要的力量支撑。
实践中还难免要面临忠于谁和忠于什么的具体问题,比如祖国、人民、事业、党派、信仰等等,都可能成为忠的对象。这又将如何把握呢?作为对象,它是一种具象;相对客体而言,它又是一种虚象。在这一层面上理解,“忠于谁”实质是一个假命题,真命题应该是“忠于关于谁的什么”,包含在对象之中的客体才是忠的指向。
以国家为例,它作为对象是指称特定领土范围及其之上的全体公民,通常由一定的组织或者机关进行治理以及在对外活动中代表国家的名义。在国家间的对外活动中体现“国家行为”,但在对内治理过程中体现的实际上是“政府行为”,而且很多国家行为只是政府行为的延伸而已。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向来不必然良善或者正确的,它可能侵害别国也可能侵害治下的任何公民,这表明面对国家或者政府其实没有当然地予以维护的充分理由。
那么,怎么忠于国家?我想唯有国家之内的全体公民共同的符合正义的利益才是忠的指向,因为全体公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体。但是相对于人类或者世界万物而言,国家也不过是狭隘的群体组织;真正广阔无边的和恒常不变的是正义,那才是忠文化最终的指向。比如党派就更显得狭隘了,党派之间以及党派与全体公民之间是没有始终一致“不二”的共同利益,那么,你将忠于或者“不二”于谁呢?所谓忠贞不二,唯有最终根本共同的正义诉求,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什么“不二”的正确或者合理。
什么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目标,什么便是值得我们在内心和行动上保持坚贞不二的东西,什么才是忠的指向。那便是天道本原,是浩然正义,是天下苍生享有生息和免除苦难的诉求;它不是人也不是神,更不是足以让我们形体屈服的强大权力,忠诚是一种坚贞的信念,它令天地为之动容,日月为之辉映,这份忠诚超越了一切狭隘的利益驱动,显示了其独有的坚贞不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