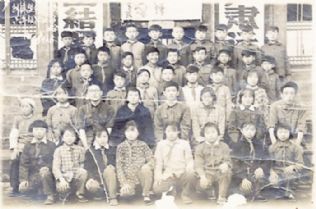在我生命的构成里,韩武堡是一组亲情的基因;
在我人生的岁月里,韩武堡是一段浪漫的时光;
在我记忆的长河里,韩武堡是一串美丽的浪花。
——题记
一
这是一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
且不说尧风舜雨,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距今也悠悠二千五百多年了。
公元前514年的秋天,晋顷公剪除豪族,分祁氏之田为梗阳(原清源,今清徐)、平陵(今平遥、文水)等七县。彼时的或后来形成的、相距一箭之遥的新营与韩武堡,却被划归两个不同的行政区,长时期分属清源、文水两县管辖。清同治年间,汾河东徙,把位于河东的大片文水县辖区揽入怀中,唯独将韩武堡与韩武村、冀家堡留在左岸。三村如游离母体之外的弃儿,被人戏称为文水的“东三省”。直到1953年,“东三省”划归新组建的清徐县,方与近在咫尺的新营村成为同一属地。1953年冬,撤区划乡,全县分为41乡,韩武堡乡为其中之一,韩武堡顺理成章成为乡治所在地。新营和韩武、冀家堡、北东社、南东社为其属村,新营村的我当然也成为了韩武堡乡的一员。以后的行政隶属多有变迁,但新营与韩武堡始终同分同合同隶转。
隶属的一致可以形成一定的同一性,但最深厚、最密切的关系是地缘。水土相连、鸡犬相闻、炊烟交汇……的新营、韩武堡在漫长的岁月里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了深厚的人际关系,形成了稳定牢固的特色地域文化。
与之基本同质的还有左近的韩武、冀家堡两村。
文化包括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要准确地阐述和诠释这片蕞尔之地的文化独特性,绝不是笔者可以胜任的。
就语音、方言而言,韩武堡和新营、韩武、冀家堡在遥迢岁月里,形成了同一的别样风格。既不同于清徐不同于祁县不同于文水,却又兼融了祁地的柔软、清源的刚硬、文水的平和等诸多特点。与近邻禅房、南北东社、北左、后营等村明显不同,惟此四村十分一致。外村人从口音上一听就知是这几个村的。许多人外出求学、工作,甚至迁居他乡,几十年乡音不改,与特色文化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浸淫在血液里。
文化之独特,可见一斑。
二
韩武堡,对于我,不仅仅是与新营水土交融、文化同一的近邻,更重要的——是我的根脉所在。
民国七年的一天,一乘婚轿在迎亲队伍的簇拥下从韩武堡村东走出,进入新营村的护村堰。轿子里坐着的新娘是赵家的长女金贤,新郎是新营村22岁的青年张仲桓。他们便是我的爷爷奶奶。从此时起,就注定了未来的我的躯体里流淌着赵家的血液,韩武堡与新营成为我生命的渊源。
祖父乳名宝源,字公瑞,出身在富裕的大家庭,他的祖父即我的高祖父,是新营出名的财主,人称六财主,有门楼院、大门院和牛房院三个院落。到祖父的父辈,家道中落,人丁殒殁。祖父失怙失恃、姐姐出嫁、哥哥外出闯荡杳无音讯。孤苦伶仃的祖父经人介绍,到祁县巨商渠家字号学徒。尽心尽责、勤奋好学的祖父经过几年的晋商文化熏陶,成长为一名年轻有为的商人。并因远房亲戚的关系,进入韩武堡赵财主的法眼,成为他的乘龙快婿。
赵财主,即我的老外祖父,名献瑸(1872—1936年),小名牛儿,人称“牛当家的”,家居村北一处三连院。外院是打谷场;西偏院为牛房院,住宿长工、饲养牲口、放置车辆农具;里院高出外院几个台阶,居住家眷。我记事时,前院、偏院已拆除,空地上长着一棵或几棵枣树。里院为小五间北屋和东、西各三间厢房的三合院,其中东厢房和西厢房一间被分给了贫农。
祖母是赵家长女,生在富户,却也是个苦命人,17岁时母亲去世,留有11岁的妹妹和8岁的弟弟。她协助父亲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两年后,父亲续弦,继母又生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祖母婚后,因祖父长年在外地工作,她便经常住在娘家,帮助继母料理家务,照管自己的弟妹。1925年,正值弱冠之年的大弟弟病亡。10年后,方逾花甲的父亲去世,家道日趋衰落。再后来,二弟联胤在儿子出生未满周岁时,被国民党强征为常备兵,一去无踪。婆媳俩守着唯一的根苗,终日以泪洗面。联胤临行前挑满的那瓮水,家人一直舍不得饮用,思念着、苦盼着亲人归来。满盛眷恋、寄予希望的一瓮清洌,在离情别恨中渐渐变浊变臭……土地改革时,这个破碎淒凉的家庭还是被划为富农。门庭衰微的赵家,成为新政权的专政对象,无奈的媳妇狠心撇下幼子随人而去,不久罹病身故。家中只剩零丁孤苦的老奶奶和小孙子旭保相依为命。
我家的境况与赵家迥然不同。自祖母过门后,家境开始好转,人丁也兴旺起来。
先是抱养了伯父继俊,1926年父亲继英出生,以后相继有了姑姑秀英,叔叔继豪和小姑秀娥。添置了土地,又购买了铁源爷爷的牛房院。祖父调往太原“书业诚”总号,并出任掌柜。
祖父带伯父到太原,送往“大兴号”杂货店学徒,把我10岁的父亲送到祁县竞新私立小学校寄读,礼拜天由父亲外祖父家的长工赶着轿车接送,直至沦陷前夕学校停办。
上述的一点血亲史,是听长辈们讲的。
亲历韩武堡离不开我的奶奶。街头巷尾,常常出现这样一道风景:前面是瞻前顾后的小脚妇人,后边是边走边玩的小屁孩。小小的我,被人称为奶奶的尾巴。
跟着奶奶,走进了我懵懂而又朦胧的韩武堡。
细细想来,我对韩武堡最初的记忆,始于两件事或者说是两个人。
老外家——老婆婆(老外祖母)。
老外祖母家一定是去过多次的,襁褓中也许被奶奶或母亲抱去过,但记忆所及之处只是当尾巴时,并且是多次的重叠:登上几级台阶进入门楼院,进入正房,迎面一支红漆大箱,西边是高大的红漆立柜,柜前一条红板橙,挨着一盘土炕。干瘦的老外祖母说不上慈祥却也平和,尽量找一点小吃给我,记忆中有晒干的高粱面煎饼、干枣等。长大后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回想往事,却怎么也感觉不到所说的地主富农婆的刁钻可恶。
东头庙——赵繁麟。
那时新营村属韩武堡乡管辖,乡政府设在韩武堡村东头庙(文昌庙)。有一次我跟随奶奶到乡里办事,走下护村堰,绕过庙宇高高的墙壁,进入朝西的庙门,再进入办公的北厢房。不知何因,发生了不愉快。乡长、韩武堡村人赵繁麟训斥奶奶,奶奶不服气,说了一句,“我家也是贫农”。赵繁麟说,“你家怎么是贫农!”在他看来,富农家的儿女亲家一定也是地主富农。转过头问当会计的新营村人张安,张安怯怯地说,是,是贫农。人高马大的赵繁麟,在当地很有影响,是多年的先进模范,后任杨房公社党委副书记。去世后,《清徐县志》人物篇为他立传。当他训斥祖母时,幼小的我一脸愤恨,圆圆的眼睛瞪着他。出了门还说,生眉动眼凶犯似的。奶奶抱起我,高兴的掉下了眼泪,她得到了孙儿的支持保护。对人们说,俺娃胆子大,连赵繁麟都不怕。多少年后说起,仍兴奋不已。斯人斯事,经奶奶的反复讲述,巩固了我的记忆。
三
韩武堡与新营一同滋育了我的童年和少年。
1958年,7岁的我开始了与韩武堡长达十年的亲密接触。
这一年秋天,我上学了。学校设在韩武堡观音庙。庙背靠南护村堰,堰外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左侧是一个天然蓄水池,俗称窖水圪洞;右侧是与之相连通的建有北房、南房的院落。
一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个教室。老师很老,姓程,也可能是陈或者是成,许是脑袋有点扁,学生叫他程(陈、成)板头。初入学的我们,在三年级大哥哥们的教唆下,很快就没有了新环境的拘谨,加入了调皮鬼的队伍。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惹得狗儿不待见”的年龄。下课钟声还没敲响,学生们要出去,老师说不住,搬一长条凳堵住门自己坐上去,挡住了门挡不住窗户,调皮鬼们从窗户向外钻。虽有“叔叔、舅舅、老先生”受人尊敬的传统说法,但捣蛋鬼们不懂,也不管什么师道尊严,反而视叛逆为荣,谁敢于和老师斗,谁就是英雄,印象最深的是韩武堡的“完了”同学。完了姓赵,年年留级,已经上了三次一年级。老师说,这个学生完了。“完了”就成为他的外号。别看他学习不好,却敢和老师对着干。有一次因淘气被叫到办公室,他和老师吵起来,竟然把学校的钉书机摔坏。钉书机当时是学校重要的办公用具,块头不大也是机器呀。这一事件影响很大。同学们都宾服他,跟着他做些恶作剧。比如把笤帚横放在半掩的门扇上面,待老师推门时坠落砸老师。比如趁别的班上课时,从后窗户悄悄地匆匆地往教室里扔一把土。
古庙寒窗,春秋十度。开蒙向上也好,蹉跎荒废也罢,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全部学生生涯。寒冷的冬天,偌大的殿堂生着一盘泥火,许多同学的手、耳都冻伤了。有的学生带着家里做的套袖袖(棉花做成的,有如半截棉衣袖子),不书写时把两手袖在其中保暖。也难以御寒。真可谓“寒窗”。也曾在凌晨与伙伴们拨开校门,点燃用蓖麻籽串起来的小小火炬照亮黎明前的黑暗,边玩儿边学习。却不可谓“苦读”。
在三年饥馑食不裹腹的日子里,我们忍着饥饿上学。路经韩武堡村打谷场,场上堆了许多玉米杆。同学们经常是翻了又翻,如果运气好时可以找到一穗小玉米。有时候我们在这一边翻捡,猪在另一边拱寻。一次发现猪找到了玉米,伙伴们一哄而上,围追堵截,硬是逼撵着猪把叼在嘴里的玉米棒子丢下。然后拾起,一起到教室围炉烧烤。
二年级时,伴着激昂的“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歌声,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组织,一名高年级的韩武堡女学生给我戴上红领巾,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几年之后,奶奶在圣母庙又为我举行了传统的、简单的另一种人生仪式——“开锁”,圣母庙位于韩武堡村东北角,俗称娘娘庙、奶奶庙。庙院中有一棵匍匐的巨型古柏,几乎占满整个院子。大殿里娘娘塑像慈眉善目、体态丰腴、雍容端庄。座像前摆有供桌,桌前方右侧放一个卦筒,筒内有卦签;供桌后方右侧放一个罄儿。一个被称为善友(庙祝)的中年或许是老年人——记忆中的他体形瘦长、身穿黑大褂、神情忧郁、沉默寡言,帮奶奶上供、烧香……好像还让我抽取了一支卦签。善友敲击罄,悠扬罄声,环绕古庙,久久不散。“开锁”仪式和顺序记忆不清,接下来或许是一开始,点火把我的十二串压岁钱红绳烧焚,奶奶收入簸箕扬去灰烬,把钱币抛洒在地。问我:要字儿(钱币有汉字的一面)还是要幕儿(白读蔓,可能是满的谐音,因钱币背面是满文)?我选择了字儿或是幕儿,并拣起所选的字儿或是幕儿朝上的钱币,其余的留给善友。奶奶用带来的新笤帚在我身上扫一遍,并祝曰:扫前心,扫后心,扫的俺娃娃平平安安通通顺顺,邪气不沾身,活到九十九。奶奶摘下我项上的长命银锁,剪断红布层层包裹成的带子(俗称“毛鞘鞘”),取下锁。
回到家,把经过神明佑护的“毛鞘鞘”挂到院中老枣树高枝上。清冷冬日,天空风微,摇曳的“毛鞘鞘”像跳跃的火焰点燃了冬天里的希望。
少年是充满幻想、喜欢冒险的年龄段。开火儿便是当时一种勇敢者的或者说是锤炼勇敢的“游戏”。冬季的田野,空旷寂静,新营与韩武堡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士是十多岁的男孩子,武器多是土坷垃等便于抛掷的硬物。护村堰是各村的基本阵地,一群人从阵地出发向对方人员进行投掷,有的小伙伴投得远,投得准,冒着弹雨勇敢向前冲,有的埋伏在渠沟中,有的利用障碍物迂回到另一侧,给对方以突然袭击。战斗的胜利是以占领对方护村堰为标志,因而保卫护村堰成为至关重要的事,一旦最后的防线被突破,便是战士的耻辱。为了荣誉,有的战士被击中,偶尔也头破血流。有两条不成文的游戏规则:一是大人不得参与,只能劝解;二是以护村堰为界,不得进村。
战场上相互开火的对手,到学校又成了同学、朋友。
小学毕业后,我没有考上普通中学,进入新开办的韩武堡农业中学。校址(教室)在韩武堡小学,与小学合二为一,其实就是韩武堡学校的一个初中班。农中学制二年,名义是半农半读,实际上也是全日制。课程与普通中学差不多,只是突出农业,表现之一是建有与农业相关的活动组,会计、农艺等组因条件有限没办起来,只有农机组凭借县属拖拉机站开展了活动。我参加了农机组,平时在校学习文化课,夏秋到孟封拖拉机站实习。
文化大革命骤然兴起,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学习文件、写批判稿、请解放军作报告、听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并组织了串连。我们一行18人在赵占华老师的带领下沿汾河而下,徒步到达晋南绛县,见到了回乡知识青年典型周明山。后从晋南乘火车返回省会太原,参加了省城学生的一些活动,如到省政府造反。
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有的红卫兵不满足于把斗争的矛头仅仅对准外面的,要在本校开展革命。目标当然是被告诬为“臭老九”的老师了,但老师毕竟是老师,师道尊严犹存。最后选择了性格暴躁、与学生略有嫌隙的某老师。红卫兵中的激进分子突发奇想,要把大字报贴到他的背上。主意出了却缺乏勇敢者,经过研究,决定由地主家庭出身的某同学完成这一任务,以示经得起考验。墨迹未干的大字报涂好了浆糊,在严厉的目光的逼迫下,趁老师转身之机,这位同学忽闪着惊恐的大眼睛,慌慌张张地把大字报粘贴在了老师的后背上。老师扭头看了一眼,没说一句话,铁青着脸大步跨出门槛。那一张象征革命的纸,随着衣襟飘摇了几下,跌落在秋雨蒙蒙的水洼里。这是韩武堡学校所谓最革命的一次行动。
三十八年前的初春某一天,我因病未到校。同学放学后告诉我:老师说了,以后就不用去上学了。过了一段时间,领到了一张由“清徐县杨房人民公社韩武堡大队学校”发放的毕业证书。签发时间:1968年3月20日。
四
时间如流水,逝去了近四十个春秋,漂白了少年头,流不去的是对故乡、对母校、对青葱岁月的记忆。多少年来,无论走得多久、多远,我的老外家、我的母校、我的老师、同学和韩武堡村许多熟悉的乡亲……缕缕乡绪如影相随。
印象深刻的教师有:严谨寡言的老校长齐子俊,兼授历史课,教我们知道了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数学老师李其亮、语文老师杨山林,还有韩武堡村的张瑞芳、赵长林、赵占华,赵吉保等老师。
韩武堡籍的同班同学有赵亮儿、赵卯林、赵成欢、张润珍、杨淑珍、赵凤凰、赵虎玲、赵玉仙、王拉锁、赵有三、赵有兰、赵连成、赵锦屏、赵星三、赵列珍、韩爱鲜、赵寿儿、张楞儿、赵发丁、猴润儿、全列儿、燕奴儿、羊着儿……多是从小同学,也有插班相遇,有的中途辍学,有的相伴到中学,还有的已是阴阳两隔。同窗时间或长或短,日后相交或深或浅或无,其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赵有三、赵星三兄弟俩,为响应学校号召卖爱国鸡蛋,他俩同守在家里鸡窝旁,等待母鸡下蛋,为一颗鸡蛋两兄弟争的面红耳赤;
有小伙伴在赵有三的作业本名字“三”上方加一点一撇,使之变成女同学“赵有兰”,惹得有三羞红了脸;
那时学校饮水由高年级挑,水井在村中心,学校没水桶,有桶的老乡怕孩子们磕碰坏,一般不愿意借出。轮到我班时,常常是赵虎林把她家里的水桶借给男生用;
赵凤凰的男同桌把玩新买的钢笔,不专心听讲。老师盛怒,命令她把同桌手中的钢笔扔到地下,赵凤凰拿过笔,怯怯地看看老师,又忧忧地瞅瞅同桌,不知所措……
还有两位难忘的韩武堡大朋友。
赵乐三,赵有三之兄,一位勤奋好学、有思想的青年。听说他有藏书,并喜欢文艺写作,便慕名而访。他独居距学校不远的一处荒芜小院,小屋简陋而凌乱,炕头摊着一些书本。在他的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知道、并见到了《解放军文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借我杂志和书,讲解写作方面的问题,如倒叙、插叙等,虽多次交往,但始终没有看到他的作品。后来,听说因地主家庭和写反动日记、画后羿射日(被诬为影射红太阳毛泽东)之故,被检举被批斗,以政治罪身陷囵圄,领刑十年,出狱后郁郁而终。风华正茂的青年凋零于阶级斗争无情的风暴里,至今谈起,令人唏嘘不已。
赵鼠祥,长我三四岁,高我两个年级。在我的眼中,他是一名英俊少年,乌黑的偏分长发,鲜艳的红领巾,尤其是明亮的双眸,充满智慧和活力。记不清怎样的初识,只是因书而时相过从。鼠祥借给我的书大部分是古籍文学,竖排、繁体字,字又小,印刷质量差,语言半文不白,读起来多有难度。虽不求甚解,却也明了大意。重要的是,鼠祥的书似乎借之不尽(其实很多是转借的)。从他那里,我借读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封神演义》等许多古典文学著作。后来,文革来了,各种书籍被扫荡一空。书为缘,书之不存,缘即淡出。我又参军离乡,联系中断。长长的几十年里,也会想起他,但一直没有再见面。直到2011年秋,才带上自己写的《清徐史话》去看望他。在韩武堡村头,遇到似曾相识的村民,询问鼠祥的住址。村民反问道,是去他婆姨家还是他小子(儿子)家?我心有不解,说,鼠祥在谁家就去谁家。身边一人插话说:“早几个月就埋到地里了!”……错谔之余,是深深的遗憾。
去年秋天,我回新营小住。一天下午放晴,推着坐轮椅的母亲外出,在韩武堡村边遇一衣履褴褛、行走蹒跚的劳作人,知他是谁家人,但搞不清是老大发丁,还是老二二发友。便试探问一句“你多大了?”不料他说:“比你老大还大嘞,你说我多大了!”不知他把我当成我的哪个弟弟了,但我知道了他就是我的一年级同学赵发丁。他见我诧异,又说:“今年65了,属虎。比你老大大一岁,他是属兔的。”
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我呢,同窗都不相识了,遑论儿童!
又遇两人和我招呼,并能叫来我的名字。从苍老的面孔上,我依稀发现了那个遥远的青春影子。不好意思问姓名,还问年龄。答曰:六十。噢,低我好几个年级呢!
青丝成雪恍若一夜间,又如从烂柯山来。时光竟这样飞逝无情,人生真得很短暂!
怎样才能留住过往,让文化得以传承?
远方游子赵国玺,情系桑梓,以拳拳赤子之心,倡导撰写村史,希望缀集为书,典藏记忆,继往开来。嘱我写点东西。赵公之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令人敬仰。遂不揣鄙薄,欣然领命,从岁月的深处撷取点滴记忆,涂抹成篇。然而,纸短情长,乡愁难尽。
韩武堡记忆,温馨而又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