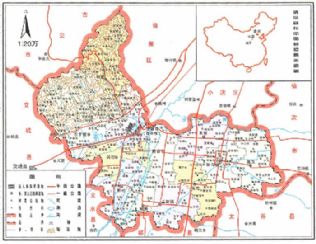西谷乡长头村:全村有2400余人,土地3000余亩,种植结构以玉米为主,葡果约占种植总面积的20%。
说起山西的历史,是绕不开汾河的,汾水流长,历经多少寒暑,这条三晋大地的母亲河,滋润了太原盆地、晋中平原,自古而今,哺育着多少三晋儿女,汾河的喜怒哀乐、历史变迁,见证了多少历史进程,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这里要说的就是汾河流经清徐段的第一个村子——西谷乡长头村。
用源远流长来形容长头的历史是贴切的,从古代农耕经济社会里,人们逐水草而居的习惯,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单从村名来说,就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讲这里是当时从太原县到清源县沿汾河的第一个村庄,故曰“长头”;另外一种说法称这里是众流(潇河、汾河)汇集之处,每到雨季发河涨,河里就会打起很大的浪头,所以叫成“长头”。孟氏家谱续谱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孟二昌老师介绍说,在祁县还有个长头村,当地人管本村叫做“南长头”,管这里叫“北长头”,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共饮一江水的缘分,让这个巧合显得神秘朦胧,充满了未知的魅力。这只是长头村名由来的两种主要说法,而不论哪种说法,都有着脉络模糊的依据,遥远难以辨识的历史渊源,为这个汾河流经的清徐第一村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亚圣之后孟氏家族
长头村孟氏是村中大族,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都姓孟,当地有句俗语“进了长头不用问,家家户户都姓孟”。虽然稍微有点夸张,却也能够看出孟氏家族在当地的位置。我们入村的时候,适逢孟氏家族进行为全宗族续谱的工作,无形中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许多便利。要知道,中华民族的悠远历史,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个人传记、家族历史的集合。从孟氏族谱来开展长头村历史文化的追根溯源,是再理想不过了。
家谱中介绍: “余孟氏闻先人相传,始祖实系亚圣之后,乃大贤之苗裔也。自前数世由山东邹县迁居关中,后复迁于晋之平阳府洪洞县。元世祖一统之后,均赋均丁,奉敕迁居于此里,属米阳都十甲,系民籍焉。”当时,这里就已经是一个有了一定规模的村落了,村子四周建有防洪的护村堰、堡墙等设施。孟和初来乍到,只能村北面的堡门外居住,后来家族繁衍壮大,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住民。据家谱记载,长头孟氏现有十七个支股,至今无大变动。孟氏家族延续了先人好学不辍的家风,有很多学而优则仕的记录,如新楼三股第三支十四世“孟宗孔,字衍泗,生于崇祯十年十月十八日吉时,终于康熙五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吉时,寿八十岁。康熙戊午年科四十四名举人籖掣四川遵义府仁怀县知县,今改贵州”(旧清源县志有载)。中街神社二十一世上世纪初在村里兴办贝露女子学校(村旧大队部是其遗址)的孟迁居的四个儿子(廷秀、廷芳、廷为、廷保)都完成大学学业,分别曾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秘书、中华民国山西省中央银行副行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大连造船厂总工程师。西三股三支的旧徐沟县警务长孟天锡(刘文炳著旧徐沟县志有载)的孙子孟国幹,曾任中华民国中央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谱中诸如此类红批时而能翻到。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厚实文化的熏陶培育,才能让孟氏家族繁荣昌盛,成为当地望族大家。然而让我们稍感不足的是,这些本来可以精彩纷呈的记录,却往往只有一两句话的介绍,给人有一种管中窥豹的茫然无措,这或许是君子实而不华、厚积薄发的传统习性使然,但难免令人有遗憾之感。联想到几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盛事的“孔氏祭祖”活动,联想到“国学”、“传统文化”的大行其道,不禁为亚圣后裔不能“兼济天下”,而心有戚戚焉。
看到如今规模宏伟的孟氏祠堂,孟氏十年续谱的家规,祠堂内存放的各种石碑和文物。我觉得,让亚圣文化在清徐大地上复苏是每一个清徐人都应有的责任,亚圣文化应该以文化产业的姿态成为更多人的事业和终身的追求。
长头的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然而紧邻汾河、潇河这两条河流的长头,在历史的进程中感受更多的不仅是水利的便捷,而是和汾河水斗智斗勇的曲折。
村委会主任梁虎根介绍说,在解放前,村里人很难享受到汾河水的好处,因为地高水底无力提取,哗啦啦的汾河水就那么白白的从村边流过去了。据今发现的碑刻史志记载,为了利用汾河水,长头人从明嘉靖四十年始就与太原县南马村合开了自西柳林取水的既济渠。清末民初,还曾为利用晋水从姚村湾南延挖修过铁板渠,留存的相当于渡槽作用的铁板方箱被入侵的日军运走。中华民国政府二十年代末,在长头段汾河上建起了第一座永久性的堤坝“铁板堰”(这个名字或许也有沿用“铁板渠”之意)。1951年又与太原市南郊区南马村、王家堡、吴家堡合开了利用潇河水的洪济渠。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党和政府又围绕着长头这段汾河水域建成了星罗棋布的水利工程:东干渠、西干渠、新二坝、敦化罐区、太榆退水渠等,可谓福泽百代,绵延不已。
至今,孟氏祠堂内还保存着既济渠碑,从河神庙中取回的镇河铁牛,碑文中记录了与邻村用水纠纷及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见这些河流对长头民众经济和生活方面的影响。即便是上世纪“破四旧”的疯狂年代,长头人还是想方设法、辗转腾挪地把既济渠碑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长头的背铁棍有了名
“东于的架火、太谷的灯,长头的背铁棍有了名。”当这句话朗朗上口地从梁虎根主任和几位老人口中一再声音洪亮、咬字清楚地说出,传入生疏的耳中,我真切地感觉到了“长头背铁棍”在这些老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不仅是表演风格、工艺制作上不同于徐沟背铁棍,连表演装扮和表演的场合也不同,相对于早已名闻天下的“徐沟背铁棍”,“长头背铁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民间艺术形式,曾长期活跃于长头村及周边的群众文化活动中。
七十多岁的孟巨宝老人介绍说,长头背铁棍相对于徐沟背铁棍历史更长,表演起来小演员的位置更高,表演时,长头背铁棍的重心在下,步伐以小碎步和“之”字形扭动为主,采用以下带上的表演方式。主要服装有各种古装、皇冠、头纱和墨镜等。到晚上表演的时候,加上随身装饰的照明设施,就称为“灯棍”。从前没有电器的时候,用的是农村人所说的“笨蜡”(蜡身较粗,不易熄灭),后来用电瓶灯和矿灯随身装饰,因为装备先进了很多,在装饰的时候,在演员们和演出设备上更加的随心所欲,有了“梨花灯”、“白菜灯”很多特色的造型,实现了更丰富的演出效果。演出时,一般至少需要十几架不同造型和角色的一同演出,完成不同的剧情。有单棍的,也有双棍(一个人身上背两个小演员)的。“长头背铁棍”的衰落有很多原因,受众不及徐沟背棍的规模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因为相对偏僻、人口少,而演出一次则需要近百人的队伍,不仅仅是演员,还有相关服务人员,化妆、服装、道具的管理都需要人。近几年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好了,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传统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长头背铁棍”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后继无人的问题,能够演出的演员,年纪最小的也在五十开外……说到这里,本来热烈的氛围忽然就消沉下来。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长头背铁棍”在他们心中的感情和位置。
在旧大队部的库房里,我们看到了锈迹斑斑、满是灰尘的演出道具和表演的服装,装在老式箱柜里的它们显得如此羸弱、老迈。年过半百的梁虎根拿起一套装在身上就给我们展示了起来,他说:“这可不是谁想玩儿就能玩儿得了的,要有步伐、节奏的表演技巧,还得有力气,只有好后生才能演得了‘双棍’……”看他投入的神态,灰尘铁锈从瘦削的身上簌簌落下,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这是酝酿已久的情绪,掺杂了故事回忆热烈浓情,对孟氏家谱编修者们默默付出的敬仰,他们都让我感受到无比强大的力量。
或许正是缘于那份强大力量的支撑,让沉寂多日的我内心又燃起一份激情,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希望未来有你与《每周一村》同行,同我们一起为清徐渐行渐远的历史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时光每时每刻都在流逝,有些东西每天都在失去。就像梁虎根主任说的那样:“有些东西,现在不去珍惜,将来失去了就说什么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