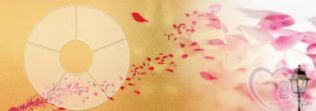大约是二千多年前一个秋天的午后。
濠水在不太远的地方流动,太阳懒洋洋地照着,田野已收割得差不多,光秃秃的土地上一群群的野鸟时起时落,间或还有一只两只野兔从身边跑过,带走一溜惊慌。
昨日夜雨霎然,路上深深的车辙中还有浅浅的潦水。
路上,两行士兵跟在一辆车后在路上拼命地跑过。辙中的潦水漾着淡淡的微漪,辙边泥土已被士兵踏踩得分外坚实。
田野上寂无一人,只有一个老头随着士兵的脚迹在后面远远的走着。
老头头上一顶尖尖的不合时宜的旧竹笠,腰伛倭着,手中一枝竹杖,既非拄又非扶,倒象一件小孩儿手中的玩具,随意在手中团团转转,或者挑弄挑弄路旁草叶上被溅上去的泥块,让被压弯的枝梗疏直身枝。
老头的走姿也煞是有趣,如果不是伛偻的腰,你绝不会分得清其是老头,还是壮年,甚或是那个王孙公子,抑或是一个贪玩的童子,是一种悠闲、洒脱、无挂无牵的自在,绝无时下里心事重重的蹒跚踟蹰,或自得意满的故作姿态,甚或狂傲无物的得意忘形。其时而快,时而慢,不象走路,而象在玩路,玩着眼前的世界。路上辙沟中的微漪,路旁草棵中的跳蝻,都能引动他的目光,让其驻足留恋,目光洒然而又凝重,飘逸而又深沉,友善而又真诚。
突然,他拐到路旁的一个小水坑边停了下来。
路旁是一个大水潦子,清彻的动人心脾,未凋的荷叶青青的绿着,还有几只荷蕾粉粉的挺出水面,骄人似的舒着腰肢,水面上水虫倏忽地在窜来窜去,荡着悠闲的自在,撩起一串细细的涟漪,周边几丛芦苇,青青黄黄地立着,白白的苇穗绽着秋的萧瑟和从容。
小水坑是和水潦子几乎连着的,也许夜雨时将其相通,小小的小坑中积注了水,竟有几尾小鱼在里面静静地游着,暖暖的阳光洒下来,在坑底弯成几只曲曲的静影。伊在水坑边蹲了下来,静静地看着鱼儿喋水,一张一张的小嘴,吞吐着淡然和悠闲。老头眉头闪出一丝欣羡,水中鱼儿的跃动却将老头在水中的画面抖成一片零乱。他接着从头上滑落的竹笠,挂在路旁一株矮矮的秃树桩上,树桩白白地露出茬口,粘粘的树液结成点点晶莹的细珠。拳把粗的树分明被快刀斩断不久。老头看看,嘴角露出不易觉察的一丝莫名其妙的表情,不知是讥讽还是怜悯。他拽了片荷叶铺在水坑边一个高出地表的土堆上坐了下来,把手中的竹杖搁在身边,身体坐得笔直,半眯着眼睛慈柔地浏视着远近,几丝花白的须髯与那张俊朗近乎光洁的面容极不相称,只有额上颊旁几线细纹告知人们伊岁月的沧桑。
太阳暖暖地照着,田野光光地秃着,鸟儿上下地飞着,蚱蜢不住地跳着,水潦清清地亮着,荷叶青青地绿着,荷蕾红红地粉着,水虫悠悠地荡着,鱼儿静静地游着……恬然如意的闲适,霎忽易辞的凄美,极天网地的情思,又怎能不着意于如丝如缕的至微。他有点如醉如痴的感觉,仿佛鲲鹏遨游南北后的一次小憩,抑或蛱蝶初飞欣羡于嫩蕊的留恋。
过了一段时间,多长,他未觉得,我也不知道,当人忘情的时候,谁会在意时间的短长?一丝风儿突然吹来的凉意,使他忽觉有点自失,拾起身旁的竹杖,准备把坑潦间的小埂捅开,但他呆住了,一把亮晃晃的锋利的剑刃分明搁在肩上,离皮肉生成的脖子只有一寸远。“庄兄,别和我藏猫猫了!”声音冰凉,象那白色的剑锋。
被叫着庄兄的老头慢慢站了起来,身形笔直,仿佛刚才的坐姿,没有了苍然龙钟的伛偻,却如临风的玉树,用竹杖敲开剑峰,转身面对着带颤的声源,抛去一丝怜悯。“还是这个样子,让我说你什么!”
他悠悠的说着,好象面对着一个做了错事的无知小儿。
来人似乎有点惭愧,将手中的剑劈着脚边的细草,将左手向后挥挥,一群锋利的刀剑如鸟兽散。“他们说你要做……”伊在辩解。油油的脸上渗出细汗,仿佛新斩的树桩凝成的细珠。
庄兄用手捋了捋颔下的须髯,须髯黑丝般飘然。眼睛怡然的看着远方。“你让我作了两天老头。也挺有意思的,只是背有点儿酸。”两天了,他象只戏着猫的老鼠,让昏头昏脑的刀剑四处乱钻而又莫钟所是。他对他的辩解不置可否,悠悠的说着,似在埋怨,似在嘲讽,又似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让胖胖的汗脸近乎无地自容。“庄、庄先生,那你作左相,我作右相……”来人汗湿重衣,觉得自己实在有点过份,若非来人的智慧,有十个也被锋利的刀剑削去了脑袋,仿佛路旁新斩的树桩。
庄先生的神情不在怡然,未正面作答,用颌指指坑中的鱼,鱼似乎未理睬人间发生的这幕谐剧,依然静静的游着,小嘴一张一张的喋着水。
来人一脸茫然,看看鱼,不知所谓,失神地看着由庄兄变成的庄先生。
“相,你去做吧!我只要鱼一样的快乐。”庄先生说得严肃而笃定。“你不有鲲鹏之志?”来人对面前的庄先生充满了迷惑,他生怕这只鲲鹏抉了他的“相”去。那种一呼百诺的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实在不舍得让人抉去。
庄先生对油光光的胖脸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又有十足的无奈,象面对着一个涉入迷途的坏小孩。淡淡地说:“楚王想让我为相。”
油光光的脸瞪圆了眼,惊愕地望看他,嘴圆圆地张着,象水里的鱼。
我捂着耳朵走了!“怎么……”他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眼睛仿佛要掉了出来。“没什么。听说鹰不吃腐烂的死耗子”。
油光光的脸有点恼怒,有点释然,更有十二分的羞惭。这事,他有过耳闻。他深悔自己太过愚鲁。他明白在士人心中目中口中算是栽到底了,急切的想挽回一点。“魏王久欲见先生当面讨教,我也恐先生错失机缘,先生可否……”他也在掩饰着难遮的窘迫。
他淡淡的笑笑,抱拳一揖:“请致意魏王,请待来日。”他知道魏王想见他是真的,而眼前的这位心里怎么想的,他更一清二楚。不然也不会有两三天的满境荒阅,他的两天老头生话了。
已没有什么好说。往日的砥砺争执已如隔世。只有专注的目光看着坑中的游鱼。
油光光的脸,抱拳一揖,被煊赫的车马载着辚辚而去,雪亮的刀剑蜂拥蚁簇,留下一片斑驳的脚印和零乱的碎草。
庄先生看着凝着细珠的树桩和零乱的碎草,露出一丝的鄙夷。
刀剑去后,田野上走出三三两两的农人,庄先生心有所触,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
他用手中的竹杖捅开坑潦间的土梗,看着鱼儿随水而去,在潦边荡起一串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