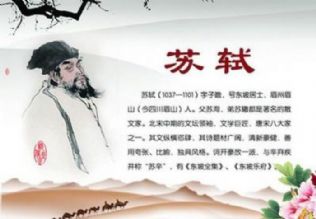我国宋代的苏东坡和辛弃疾,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在词的发展史上,人们把苏轼、辛弃疾看作是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以“苏辛”并称。然而,同是豪放词派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词在内容方面、形式方面、风格方面均有明显差别,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苏词超脱旷达,辛词沉郁豪壮。苏辛二人的不同处世人生态度,形成了苏词超脱旷达,辛词沉郁豪壮的两种豪放词风。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的相似之处(一)都有力开拓了词的内容。
在词的发展史上,人们把苏轼、辛弃疾看作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作家,以“苏辛”并称。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所以刘熙载说:“东坡词似是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使词内容更加扩大,题材更加拓宽。辛弃疾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要广泛得多。辛弃疾还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经传、辞赋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对豪放词做了更深的开拓和大力的发展,把词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词中,作者高呼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二)都集中体现了豪放的风格。
苏辛词中都饱含着浓烈奔放的豪情,流露出积极的人生态度,表达了词人对生活无比热爱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正是他们的这种豪情壮志,决定了苏辛词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而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到“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表达了决不投降、坚决抗金的决心。他借赞扬杰出的历史人物,讽刺苟安求和者,表示了坚决抗金、收复中原的坚强信念,表现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词中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轼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都流露抒发了悲愤的情愫。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都受尽了现实的迫害和打击。苏轼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庭,家庭的熏陶使苏轼从小就树立大志。1056 年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四川到京城应考,一举成名。其文章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赞,称赞苏轼是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自此一举成名,开始了仕途生涯。然而苏轼在仕途上并不如意,由于卷入党派纷争,受到排挤,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被贬和流放当中度过的。因此在被贬和流放的时间中,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成为苏轼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感基调,在他的豪放词中这样的情感随处可见。辛弃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 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但此后,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只能寄托于诗词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作者失意闲居信州时所作,无沙场征战之苦,而有沙场征战的热烈。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位沙场点兵的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不仅为了“了却”君王的洗雪国耻、恢复中原的“天下事”,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能施展雄才大略,赢得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生前身后名”。然而一句“可怜白发生”,一下从理想的高峰跌入现实的深渊。词中通过创造雄奇的意境,抒发了杀敌报国、恢复祖国山河、建立功名的壮怀,结句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
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差异(一)内容方面
从内容上,苏生活在民族矛盾不太突出的北宋,抒发怀人、念友、际遇、人生感情的题材较多。而辛弃疾生活在偏安一隅的南宋,作为一个爱国词人,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题材不少。苏词对于痛苦、愤慨的抒写是隐蔽的、含蓄的;苏词种种忧郁的情绪总会在词人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中被排除和化解,最终也会表现出坦荡潇洒、乐观的情怀。“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从中可以看出词人健康开朗的思想情绪。作者通过想象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琼绝尘寰的奇景,再从景物的自然更迭引到人事的流转变迁,以自然境界的清澄辽阔反映出作者思想境界的开朗廊达。语言脱却柔靡,不落俗套,是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辛词则不然,其抒写痛苦和愤慨是溢于言表的;所流露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深切,那么激越、苍凉!读辛词,自有一种热血奔涌、悲壮慷慨、甚而至于潸然涕下的激情,英雄末路的无限孤独和对现实的怨愤溢于言表,那种孤独和怨愤,是不能排除也是无法排除的! “神州毕竟,几番离合”。(《贺新郎》)“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魂没,弦解语恨难说”(《贺新郎·赋·琵琶》),如呜咽悲歌,感慨悲凉。说到底,苏词中的悲愤和痛苦,毕竟只是苏轼个人怀才不遇情绪的表露,加之苏轼固有的开朗和放旷的性格,自然会有苏词旷达、飘逸的风格。而辛词中的忧愤之情,悲伤之意,远非辛弃疾个人之悲痛。辛弃疾一生以报国为志,却被投闲置散,一腔爱国激情无处可发,他的忧愤不只是从个人得失出发,而与当时的民族灾难是一致的,故有辛词沉郁、豪迈悲壮的风格。辛词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笔触描写。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词有了很广阔的社会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辛词所承载的内容,远比苏词要沉重、深刻。
(二)形式方面
苏轼在语言上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律限制,“‘以诗为词’,从而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语自胡寅的《题酒边词》)”。苏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浪漫的把酒赏月的美丽风景画面,色彩浓淡有致,画面动静相宜,有作者人物、有朱阁绮户、有青天橙月、有月宫的琼楼玉宇的静物实景;又有清风吹拂、有月光“转”“低”“照”;有“把酒”相“问”、有“起舞弄影”的动感镜头,更有生动的言语表达和内心思想活动的虚实写照。全词情感真挚而又情景交融,韵律激昂而又气势豪迈,结构严谨,用词干练,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浪漫豪放的词风。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辛词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用典,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一连用了五个典故,正是运用这五个典故,寄托了词人对南归四十三年的沉痛经历的总结,是他才兼文武,富于韬略的突出表现。
(三)风格方面
从风格上,东坡通过词作体现的是宽广的胸怀、高雅的气度和不羁的性格。而透过稼轩的词作能看出词人的悲壮气节和力度蕴含。所以才子元帅陈毅说,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均。正如王国维所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旷者,能摆脱之谓;豪者,能担当之谓。能摆脱故能潇洒,能担当故能豪迈。
“能摆脱,故凡事总由窄处往宽处想”,苏轼就是这样。苏轼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屡遭贬谪,当时的恐悸、孤独、苦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能彻悟人生,乐观对待生活,这使他的词有一种旷达的超脱气势,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写于被贬黄州时期,三年的谪居生活,长官同僚的厚待,乡野村夫的尊爱,亦能略略慰藉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东坡的心从刚被贬谪的绝望中逐渐苏醒,心态变得缓和、宁静。“何妨”表现了词人的淡定,映衬词人的态度是那么从容不迫,潇洒自得,且吟且啸,徐步向前。“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进一步写出了他的旷达与倔强,并将自然界的风雨与人生道路上的风雨联系起来。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表明了他那种随缘自得的宁静心境和旷达的胸襟。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妥协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故而在辛词中形成辛词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风格。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词中所刻划的形象是壮烈勇猛的,所表现的思想是奋发激昂的,最后一句使全词的感情发生急剧变化,它是一声无可奈何、感慨万端的叹息,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这一转折,使上面所写的梦境理想成为幻想,全都落空。全词至此也由“雄壮”而变为“悲愤”。最后一句与开头的“醉里挑灯看剑”相呼应,都是叙写现实生活与感受。这首词着重表现他报国欲死疆场的愤慨,犹如一曲悲壮慷慨之歌。词人写梦境中的豪壮雄伟,大显身手,极力渲染威武雄壮的军营和激烈的战斗场面,风驰电掣,惊心动魄,而表达的情感却是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
苏轼和辛弃疾同为豪放词的杰出代表,他们对豪放词的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对古人还是对今人来说,苏轼和辛弃疾历来都是被人们所称道所喜欢的。如果说苏词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位“仙者”,那么在辛词里则更多的看到的是帝王将相类的“志士”。不论是什么样的风格,都是最直接的感情的流露,从而汇聚成词史的河流,绵延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