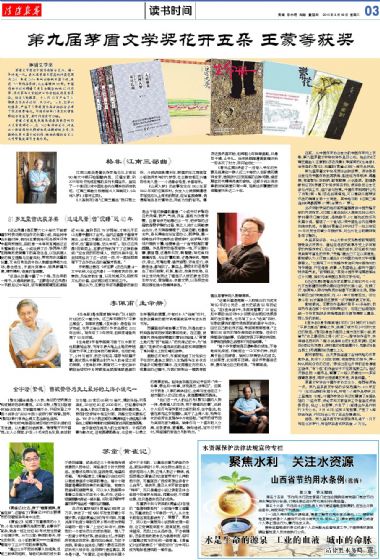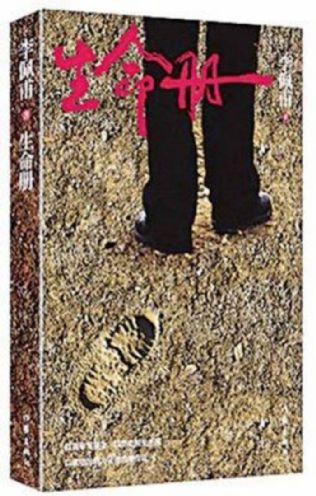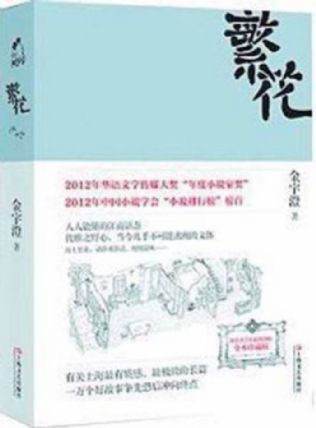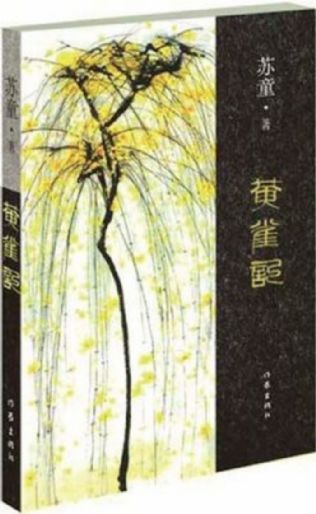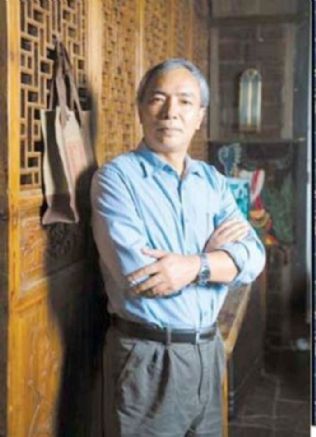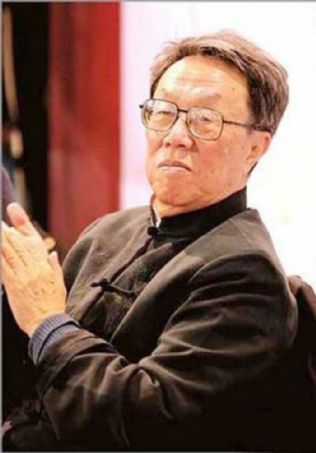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4年评选一次。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围为2011年至2014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共有252部作品参评,比上届增加74部。中国作协书记处聘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2位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评奖委员会。经过5轮投票,于8月12日产生了10部提名作品并进行3天公示。16日,经第六轮投票,产生了5部获奖作品并向社会公布了实名投票情况。中国作协专门设立纪律监察组全程监督,并对评奖进行公证。
茅盾文学奖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自1982年开评至今,评选出一批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力作,为激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格非《江南三部曲》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人面桃花》是“江南三部曲”的开卷之作。小说讲述晚清末年、民国初年江南官宦小姐陆秀米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小说悬念迭生,余韵悠长。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在浴室卖澡票,偶遇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并成为他的秘书。谭功达虽然喜欢她,但却担心年龄等差距,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后来姚佩佩遭高官强奸后一怒杀死了对方,并开始逃亡……《春尽江南》讲述了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度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这部小说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只有一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幅度则长达二十年。
81岁王蒙首次获茅奖《这边风景》曾“沉睡”近40年
《这边风景》是王蒙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因各种缘由未曾付梓,但在《王蒙自传》和各版本评传中都有所提及,因而是一本早有耳闻却迟迟未露面的小说。小说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带有历史沉重的份量,又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塑造得极为生动,悬念迭生,矛盾冲突集中,独具新疆风情,情节精彩,语言机智幽默。“这是从坟墓中翻了一个身,走出来的一部书,从遗体到新生。”王蒙在《这边风景》一书的后记中写到,该书曾被雪藏在柜橱里近40年,直到自己78岁那年,才被儿子王山无意中翻找了出来。当时正值妻子崔瑞芳离去,尘封之作重见天日,勾起了王蒙无限感怀,他“重读旧稿、悲从中来”。在《这边风景》的首页上,王蒙还特别写下了这样的献词:“纪念我的初恋情人,我的终身伴侣,与我共同经历了这一切的一切,并一再鼓励我写下了此作的永远的崔瑞芳吾爱。”
作家雷达曾在《评王蒙<这边风景>》一文中谈到,《这边风景》一书拥有历史的、审美的、风俗史的价值,以及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应该被加进文学史之中。
雷达认为,王蒙创作该书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他对新疆的喜爱:“小说中对伊犁的自然风情,物产,气候,风俗,都极为欣赏夸赞。且看写伊力哈穆归乡一节,进伊犁的过程就是赞伊犁的过程,车上人说什么阿勒泰山太冷,冬天得提着棍子,边尿边敲;吐鲁番太热,县长得泡在浴缸里办公,而伊犁,插一根电线杆子也能长出青枝绿叶,说伊犁人哪怕只剩两个馕,也要拿出一个当手鼓敲打着起舞。作品写劳动场面堪称一绝,不论舞钐镰,割苜蓿,还是拌石灰,刷墙壁;写吃食则满嘴流香,无论打馕和面,还是烤羊肉,喝啤沃,总之,吃喝拉撒、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宗教生活,都写到了。事实上,最根本的还是写出了他们幽默,机智,豁达,浪漫的性格,总体上生动地表达了维吾尔人民的原生态的生存方式、思维理念、宗教文明,以及积淀在其民族性格中的精神原色。”
李佩甫《生命册》
《生命册》是李佩甫继《羊的门》、《城的灯》后的又一部力作。这三部书被称为“平原三部曲”。李佩甫透露,《生命册》是在他59岁完成,花甲之年出版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出版)。写作用了3年时间,但积累储备则用了50年时间。《生命册》作者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
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这部长篇是用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来写50年的心灵史、成长史或者50年的记忆。”在《生命册》中,李佩甫描摹了20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也书写了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的坚守与迷失。回忆自己的创作历程,李佩甫颇有感慨:“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存在很多困难,很多时候都是在编故事,但是我发现了平原这块领地,平原就在我身边,我根本不用去编故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熟悉的领地,不停地深扎深挖,则能挖出一口文学的井,找到属于自己的源泉,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成功。比如莫言,比如贾平凹等。很多作家都是这样,最终写出自己的成果。”李佩甫说。
金宇澄《繁花》曾被赞誉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
《繁花》里全部是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构成城市的多彩景观。2012年秋,《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文学圈反响不小,并很快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翌年,《繁花》单行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繁花》的笔触落在被忽视的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以大量的对话叙事,缓缓铺开市井画卷。主人公阿宝、沪生、小毛来自各阶层,叙述时空交错,20世纪60到70年代,情欲张扬,动荡离乱,20世纪80至2000年代,已经是浮华岁月,各色人物依次登场,人情世相秋毫毕现。人物在时空穿梭中相互对照,两部分空间最后汇合。100多个人物之间的纠葛演绎至小说结尾,以准备拍上海题材电影的法国情侣的出现而宣告落幕。金宇澄站在说书人的立场写作,小说的叙事为散点式,没有高潮和悬念,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主线。恰如金宇澄在后记中自陈:“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但其对于物象、人事的具体回忆,全部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的记忆相合,其描摹精微而具体。“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与《繁花》里的人物一样,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不普通的故事”,谈到个人经历与写作素材之间的联系,金宇澄说。他曾在黑龙江农场插队,离开了上海八年,特殊年代的经历在其写作中亦有投射。“城市的细节因为离开而更为醒目。就像你与一个喜欢的人分离,印象更深,更逼真。换句话说,城市对于农村,有很强的渗透力与影响力。”
苏童《黄雀记》
《黄雀记》之名,源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暗喻了《黄雀记》中的主要情节的交错复杂与命中注定。
《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分为三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章的标题暗示了三个不同的叙事视角。“通过三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组成三段体的结构,写他们后来的成长和不停的碰撞,或者说这三个受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命运,背后是这个时代的变迁。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某种程度上,《黄雀记》由此也可以看成是诸多小短篇的集合,每个小短篇都是精致而优美的苏童风格,有南方的湿润和幽暗气息,可以令人耽溺其中像静立在临水的悠长小巷。然而,这些小短篇要最终形成一部长篇,好比很多意味丰富的照片组合成一幅恢弘的壁画。
此次苏童获奖的《黄雀记》共有26万字,讲述了一桩1980年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谈起《黄雀记》的写作动因,苏童说源于他青少年时在家乡苏州街坊亲眼目睹的一起个案,“上世纪80年代,我熟悉的一个老实巴交的街坊男孩,卷入了一起青少年轮奸案,据说是主犯。涉案的所有男孩的家长,都在四处奔波,为孩子洗罪。案情众说纷纭,而那个最老实的男孩后来入狱多年,他的罪行是否真实,其实是个谜。”苏童说,这也是他的长篇小说中不多见的、以真实故事为原型的作品,前后共耗时3年,关注的也是社会上很多见的小人物、边缘人物这个群体,说起想通过《黄雀记》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时,苏童直言:“我没有想给读者什么启示”。他表示,自己从来不做读者的“导师”,而只是通过小说让读者去体会他眼中的世界与现实。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他只是提供自己的视角。
苏童表示如今获奖的《黄雀记》在他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当中意义蛮重大。苏童说他这个年龄的一代人,从小生长的街区现在都消失了、倒塌了、颓废了,所以他一直想用小说的形式造一条街,让它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深,而且让它永远存活,不会被强拆。这条街虽然被命名为香椿树街,但可以理解成南方的任何一条街道。《黄雀记》恰好就是这个“造街运动”当中可以成为地标性建筑的一部作品。
日前,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作家网上获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已公布。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共5部作品获奖。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采用实名制投票,评奖委员会主任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副主任为李敬泽、阎晶明,有孟繁华、陈晓明、谢有顺等59名委员。根据最新修订的《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评奖委员会主任参与评奖工作,但不参与投票。中国作家网同时公布了终轮(第6轮)实名投票情况,可以看到5部获奖作品的得票优势十分明显,其中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获得最高票57票(全票为61票)。
此次同时获奖的格非和苏童都曾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江南三部曲》由《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组成,是格非于2011年完成的系列长篇小说,描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演变轨迹。苏童在《黄雀记》中讲述了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对当代社会的精神现象做了解析。
本届茅奖评委、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曾经在语言的叙事形式上多有探索的先锋作家们,经过几十年的成长,已经成长为非常具有丰富性的作家,“先锋”概念已不足以来概括。谢有顺认为,《江南三部曲》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有重要意义。“它展现了一个先锋作家如何向中国传统的写作转型,并在语言、叙事、人物塑造上,都有中国的特点和气派。”谢有顺说,“其实中国作家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何传承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
《这边风景》是著名作家王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因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出版,在2013年才首度面世。这也是今年81岁高龄的王蒙第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
谢有顺说,王蒙的作品虽然写于40多年前,但因为作者在那个年代的特殊经历,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作家能把多民族混居的生活写得那么真实、那么生机勃勃。
《生命册》是李佩甫继《羊的门》《城的灯》后的“平原三部曲”巅峰之作,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繁花》是金宇澄的上海方言长篇小说,被誉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除获奖作品外,获得提名的另外5部小说是林白的《北去来辞》、红柯的《喀拉布风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范稳的《吾血吾土》和阎真的《活着之上》。
谢有顺发现,此次茅奖涵盖了各种风格的作家和作品,且对个人性比较强、有探索性的写作,持一种认同和包容的态度。“茅奖过去给外界的印象是很主旋律,‘有个性’的作品似乎不在其视野之内。但这次提名的10部作品,颠覆了一些人的看法——茅奖强调思想性,同时也很强调艺术性,两者并重。”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每四年评选一次。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范围为2011年至2014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共有252部作品参评,比上届增加74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聘请了全国各地的62位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评奖委员会,经过5轮投票,产生了10部提名作品并进行3天公示。8月16日,经第6轮投票,产生了5部获奖作品,并向社会公布了实名投票情况。
据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每位获奖者将获奖金5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