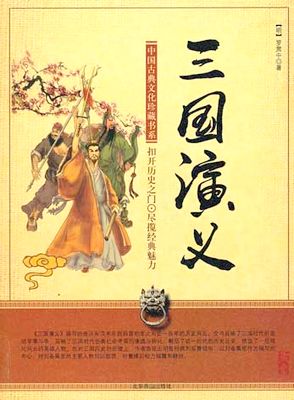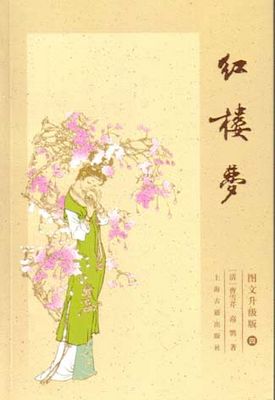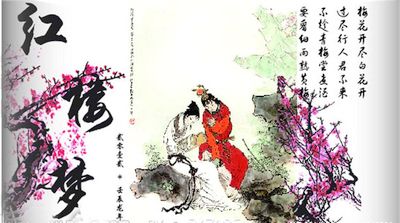如果说《红楼》是一出痴男怨女风花雪月的春梦,那么《三国》就是一场文臣武将争权夺利的演义,表面看它们风格内容迥异,实质上最终殊途同归,表现了同样一个主旨——于人生,人生苦短,荣华富贵浑是梦;于人事,人事无常,计较到老一场空。所不同的只是《红楼》略感温馨,而《三国》则非常血腥。《红楼》里空空道人唱着《好了歌》,甄士隐做注说: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自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冷,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三国》则有杨慎的《临江仙》开宗明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情绪都是“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目的都是“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再明白不过了。
人都说宝玉叛逆,不爱功名,所以在他生活的那个家族里备受诟病,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纨袴膏粱的典型。其实宝玉不爱功名才正常,他能干的祖先给他创下如此庞大的基业,豪宅华屋,仆婢成群,锦衣玉食,门当户对缔结姻亲更是强强联手——一落地就置身在功名砌就的温柔富贵乡里,怎会有对功名的渴望?水中的鱼儿还稀罕水?还是天上的飞鸟还向往天?陈胜是在被发配押往渔阳途中质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项羽是在看到秦始皇出游的壮观场面产生“吾可取而代之”的宏愿的;刘邦也是在这个时候感慨“大丈夫当如此”的……也就是说,人所拥有的东西,已不再对人产生诱惑;而彼岸,才是每一个人难以割舍的向往。
但是,宝玉不是一个反面形象。他的意义在于告诉世人无论是荣华富贵还是风花雪月,最终都是一场劳心费神的春梦。他以他的悲剧宣告了祖父辈们的暂成终败。毫无疑问,曹雪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红楼梦》,从它出世起就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醒世恒言。《红楼》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三国》则是三个家族的兴衰史。
作品从汉末宫廷斗争开始,到十七路诸侯互相倾轧逐鹿中原,再到魏蜀吴鼎立后的尔虞我诈三国争霸,各路英豪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但最终结果是司马氏一统华夏,建立了大晋。这虽然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但又确凿是历史的真相。
曹操自己一生辗转颠沛殚精竭虑,父母家人被杀,辜负了那么多人。生有二十五子,早死的战死的不说,剩下有才干的互相猜忌手足相残,平庸的被分封各地,七零八落徒有虚名,受禁令防备,形同囹圄,求做平民而不得。明帝曹睿之后,三少帝曹髦、曹芳、曹奂享国日浅,被杀被欺凌。这绝不是曹操出生入死拼杀一生想要的结果,但事实就是这样残酷。
刘备从布衣起家,起步更加艰难,其经历遭遇也更加坎坷更为狼狈。他号称匡扶汉室,从事征伐,有愧狼狈阴暗的事多,风光得意磊落的事少;号称承继正统践位称帝,可惜宝座还没有温热,就寿终弃世。生得虚伪,死得有憾,这一生该有多么失败!可恨的是他的耻辱没有随着他的死而结束,最终还以刘禅无能懦弱乐不思蜀而贻笑天下。当然这更不是刘备苦心积虑流离一生想要的结果,但世事如此,人力实在难为。
孙坚十七岁的时候因单独智斗海盗而声名大振,少年成名的消极后果是会使人恃强好勇无所畏惧,所以在攻打刘表的时候,他单身独骑冲到岘山而身死敌手,英年早逝。长子孙策回到江东,继承父志,招贤纳士,以图大业。他借兵发展自己的势力,很快便由弱变强,统一江东。但他性急少谋、轻而无备,刚刚二十六岁就死于小人之手。之后孙权继承父兄基业,成为一方诸侯,并登基为帝。但孙权晚年糊涂,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无常,陆逊等重臣都受到牵连,内政十分混乱。长子孙登夭折后,孙权先是废了三子孙和,又赐死四子孙霸,最后立幼子孙亮。孙亮为帝时年仅十岁,等他长到十六岁想要亲政时,与权臣孙綝发生矛盾被废,两年后死于非命。后孙权的第六子孙休继位,七年后去世。孙休死后,孙和的儿子孙皓继位。孙皓荒淫无度,穷兵黩武、刑罚放滥,大臣诸将,人不自保,以致亡国。孙皓死年42岁。这样的结果,也绝不在孙坚的意料之内。
历史是不容回头的,假如允许回头,不知当时踌躇满志觊觎天下的诸位前辈,会选择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红楼》里的人,善终的极少。用《三国》里的话说,是孔融儿子说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三国》里,一个人能善终也很不容易,无论智愚贤不肖。天不假年如郭嘉,外宽内忌如袁绍,好勇逞强如孙坚,智暗懦弱如刘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天意如此或者性格使然。然而聪明如杨修、正直如荀彧,忠贞如沮授,骁勇如典韦,智勇皆备如邓艾……这些人也不得善终,生逢乱世固然是客观因素,但本人的追求才是那个最根本的原因。
邓艾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有口吃的毛病;曾在汝南牧牛。但他从小有大志向,决心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初凭才学被举荐为典农都尉学士,因口吃未能迁升。后来偶遇太尉司马懿,司马懿赏识邓艾的才干,任他为太尉府掾属,后升任尚书郎。
邓艾曾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一是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以便灌溉农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疏通漕运;二是在淮北、淮南实行大规模的军屯。司马懿采纳并实施了他的意见。这两项举措使得曹魏兵精粮足,又没有水害。三国后期,曹魏政权能始终保持实力最强,邓艾的许多政治主张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邓艾内能安民,外能定邦,文韬武略,智勇皆备。十几年中,他与蜀将姜维对峙,所在之处荒野开辟,军民并丰,战无不胜。尤其最后,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置自身安危不顾,身先士卒,偷渡阴平,攻破涪陵及绵竹,致使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邓艾的人生轨迹一路向上,至此达到顶点。
《红楼》里秦可卿死前劝告王熙凤,“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高必跌重”,但显然凤姐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她出尽风头、使尽手腕,最后免不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结果。
邓艾也是一样,他可以得意洋洋地统帅千军万马,可以风光无限地驰骋沙场,可以一往无前地攻城略地,可以无比自豪地接受刘禅投降,以“素微”之躯跻身高位。然而他不善自保,最终为钟会构陷,父子二人同时被杀,成为上层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陆游说:“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缠裹。”这种入世的悲哀,难免让人想起那些出世的安然。
春秋时,楚王派使者带着一百镒黄金、两辆马车的东西去礼聘接舆。使者说:“大王请您帮助国家治理江南。”接舆对使者微微一笑,继续做手中的活计。使者无从置喙,只好回去。接舆的妻子回到家,看到门外车子的辄印,问接舆:“先生过去甘于平淡,怎么现在却耐不住寂寞了。刚才是谁来了?”接舆答到:“是楚王派人来请我做官。”妻子问:“你答应了?”接舆说:“人们大都想着富贵,你也不会讨厌它吧?”妻子说:“有道之人,不会因为困窘改变自己的准则,不会因为贫穷改变自己的言行。咱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耕我织,自得其乐,这样多好呀。常言说:家鸡有食汤锅近,野鹤无粮天地宽。”接舆说:“这我知道。可楚王要抓我入鸡笼,我又如何呀?”妻子说:“楚王让你做官,你不答应,却也是件麻烦事。看来,我们只好隐姓埋名,远离这个地方了。”于是,接舆背着锅碗,妻子扛着纺织的工具,逃到杳无人烟的地方隐居起来。
南郡襄阳人庞公就是这样做的。刘表数次延请,给他侯爵之位,他都不去屈就。刘表说:“你保全了你一个人,为什么不保全天下呢?”庞公笑着说:“鸿鹄在高树上筑巢,晚上有栖息的地方,鼋鼍在深渊下面藏身,晚上也可以得到休息。取舍行止是人的巢穴,我们各自有栖宿的地方,天下并不是我所能保全的。”因而与妻子一起在地里耕作。刘表问:“先生住在田亩之中,不肯出来做官,能留给子孙什么呢?”庞公答道:“世人留给子孙的是使人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钱财,我留给子孙的是耕读传家、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只是遗留的东西不同罢了。”刘表叹息而去。之后庞公与妻儿一起登鹿门山采药不返。
这和庄子宁愿曳尾于涂中而不愿居于庙堂的追求是一样的,与其说是清高,不如说是为了安然和久长。邓艾不过是一个例子,纵览整个《三国》,如此下场的王侯将相不知道有多少,而历史,是惊人地相似的。
《红楼》里有一支曲子叫“恨无常”,写的是皇妃元春:
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治世从来都是“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而乱世确实是成就英雄的好时候,许多出身低微而才华出众的人,都能借此机会出人头地、建功立业。“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所恶者贫贱死亡也。”世事人情如此,又有几个能抵挡得了功成名就荣华富贵的诱惑呢?
根据鱼豢《魏略》的记载,文帝曹丕的弟弟曹干年龄小,见到文帝,常管他叫爹。文帝就对弟弟说:“我是你哥哥。”文帝很怜惜这个小弟弟,每为之流泪。
许多资料都记载,司马昭宴请刘禅,故意安排蜀国的节目,在旁的人都为刘禅亡国感到悲伤,而刘禅却欢乐嬉笑,无动于衷。有一天,司马昭问刘禅:“是否会思念蜀地?”刘禅回答说:“这里很快乐,不思念蜀国。”知道了这事,随侍刘禅的郤正就教导他说:“如果司马昭再问起,你应该哭泣着回答:‘先人的坟墓都在蜀地,我天天都在惦念着。’”后来司马昭再问他时,刘禅便照着郤正教他的话回答。司马昭说:“这怎么像郤正的语气呢!”刘禅听了,睁大眼睛望着司马昭说:“您说的没错。”左右的人都笑了。
而孙皓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孙皓仿效刘禅降晋后,贾充对他说:“听说阁下在南方挖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孙皓说:“有作为臣子却弑杀他的国君以及奸险狡诈不忠的人,就对他用这种刑罚。”贾充听后,沉默不语,非常惭愧,因为贾充曾带人弑杀魏帝曹髦。而孙皓则脸色不变。
晋武帝派人把孙皓以及投降的吴人带来相见。孙皓上大殿向晋武帝叩头。晋武帝对孙皓说:“朕设了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说:“我在南方,也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陛下。”又有一次,晋武帝问孙皓说:“听说南方的人喜欢做尔汝歌,你能作一首吗?”孙皓正在喝酒,乘机举着酒杯劝晋武帝喝酒说:“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晋武帝非常后悔让他作诗。
又说邓艾口吃,说到自己往往语称“艾艾”。晋文王跟他开玩笑:“你说‘艾艾’,当是几艾?”邓艾回答说:“‘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兄弟有爱如此!刘禅单纯如此!孙皓才识如此!邓艾机敏如此!——如果不是有一个罪恶的功名富贵横亘在人与人之间,人性的美不曾在权势和金钱面前沉沦泯灭,那么这是一个多么温馨愉快的人世呢!
世人看《红楼》,常常溺于风月;看《三国》,又常常耽于权谋。看不到它们儿女情长、乱世风云之后隐藏着的关于世相人生永恒的真相,无异于赏花却只看见花盆下面那个用于陪衬的花架子。
《红楼》里说:“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三国》里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殊途同归!不过是富贵易去,功名虚幻,繁华散尽之后的无限怅惘与寂寞。
古人说:“人生无常,为欢几何?”又说:“百年如流矢,生命若昙花。”但人世的荒谬就在于虚妄,而人生的悲哀就在于将虚妄当真实,执着于对虚名和外物的追求,因之役使自己的身心,辛苦疲惫。奸险恶斗,自私残暴,骄奢放纵,妒忌陷害……人生的苦恼、人世的动荡由此而生。
然而活在当世里的人,又有几个能现下就明白呢?既然人生根本就无法回头重新来过,那就只能将遗憾留给自己,将谈资留给将来的某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