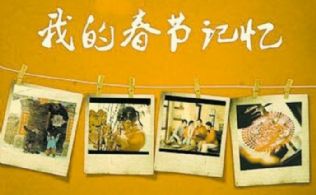1949年1月28日,是农历戊子年的除夕。这是家乡解放后的第一个除夕,全村家家户户喜气洋洋过除夕,欢天喜地迎新年,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美好记忆。
天刚亮,公鸡还未报晓,鞭炮声已经在村子里响起。当我走向门外时,十字街头的秋千已经有人荡起,下面站着的人有的高声欢呼,有的不停地向天空抛掷着点燃的炮仗。我与哥哥也赶快在秋千底下排了队,不一会儿,我们便踏上了秋千的踏板。我俩全力合作,在双膝不停地伸屈的运动中,荡上了高空。微风从耳边闪过,浑身上下一阵清爽,那种快乐即刻由心底传到了脸上。
早几天就搭起的九曲,已有好多小朋友兴致勃勃地在里面追逐着,欢笑着。街头巷尾穿着新衣戴着新帽的小朋友们成群结队手里提着“滴滴金”闪闪发亮,愉快地做着各种游戏。走在街上的人们互相问候着,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笑容。年轻的鼓乐手敲起了欢快的锣鼓,彰显出了翻身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给翻身得解放的村子里,平添了欢快的节日气氛。
太阳升起来了,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在有人张贴着红彤彤的对联。各家各户的门楣上方,张挂着五光十色的花红与彩带,将解放后的新农村,装点得生机勃勃喜气洋洋。
除夕之日蒸年糕贴对联是我们家乡的习俗。那是在刚刚解放后的日子里,邻居们就商量着在麦田里回墒了软糜子,为的就是在除夕日,做年糕吃。刚进腊月门,乡亲们将软糜子先碾成软米,在除夕的前几天,就用温水淘洗干净,晾在家里,当晾到半干时,家家户户就轮流在石碾上碾制糕面,准备在除夕之日蒸年糕。父亲在前几天,就将珍藏着的红小豆、豇豆浸泡在盆子里,吃完早饭后,便将这些真材实料煮熟捣烂,在里面掺上了红糖、玫瑰酱,做好了美味可口的糕馅。母亲是蒸年糕的好手,只见她将金黄金黄的糕面用少量的温水搅拌起来,轻轻地握成小块,放入蒸笼开始蒸了起来。掌握适量的水份是母亲的拿手技艺,蒸上十分钟后,母亲便将那蒸熟的糕面放在陶瓷盆子里反复揣压,那金灿灿的糕面软硬正好黏稠适度,父亲和母亲便在手里醮上食油开始捏制年糕。中午时分,我们弟兄三人,便手里端着期盼已久的油炸年糕,向本家的爷爷和邻居的家里送去。街上随处可见到三三两两赠送年糕的身影。解放后的家乡,没有了战争的恐惧,没有了逼粮逼款的威胁,乡亲们就这样互相赠送着,快乐着。
在父母忙碌着的同时,哥哥带着我和弟弟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做着准备已久的“砂罐子”。“砂罐子”是我们家乡的一种焰火。一般是生铁铸造而成的。心灵手巧的哥哥,将我家的一个旧铁茶壶底部捣了一个小孔,里面用胶泥好像套灶火一样套了厚厚的一层。那些需要的火药,也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木炭是我们用拣拾来的枣树枝烧的,尿碱是我们从村子里各个厕所的尿池边刮取的,麦麸子是家里的,硫磺是家里旧有的。我们将这些材料放在一个石头瓮盖上,用斧头捣,用石头碾磨,用小箩子筛,搞成细细的火药面,装在“茶壶砂罐子”里。
夜幕降临了,从远远近近的邻居家传来了各种各样燃放爆竹的声音。我们全家也都站在院子里,当哥哥将我们精心制作的“砂罐子”点燃时,那绚丽的火花好像一座奔腾汹涌的彩色火山,直直地冲出了我家的屋檐。那些彩绘在横披上的人物也兴奋地飞舞了起来。那威武的武松高举铁拳,好像要砸碎那世间的一切妖魔鬼怪。那手舞金骨棒的孙悟空,好像也升向高空,与我们在这太平世界里同乐。那团扇半遮面的林黛玉,好像飘飘然地来到了人间。那嫦娥轻纱曼舞升向月宫。“砂罐子”照亮了我家的大院,照亮了半边天,也照亮了解放后的村庄和人们的笑脸。
欢乐的除夕!欢乐的除夕夜!我永远地牢记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