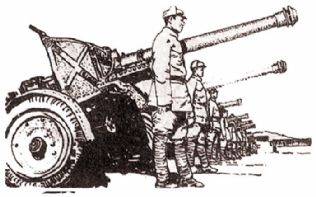我叫时光明,小名叫拴狗儿,今年88岁。家住清徐县东罗村,距县城25公里,抗日战争期间是晋东南、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来往的交通要道之一,也是敌占区中的游击区。
1944年正月,天气异常寒冷。街上很少有人。刘景圣的修车铺外,虽无修车的事,修车的小徒弟却一直在门外溜达,村里人都知道,这是景圣家又来“客人”了。我装着玩耍的样子,走到院子里,推开正房门闯进屋内。成栋叔见我进来,忙起身说:“拴狗儿,出去耍吧!来这里作甚?”“我要当兵!”一语道出,惊动了屋子里的七八个人。炕沿上坐着的人对我说:“小孩子,当什么兵?”“我要当八路军!”又一位看来像领导的人对旁边一位同志说:“先让他出去,看好他,不要让他乱说话。”他们把我哄了出来,交给在门外溜达的小伙计。过了一阵,他们把我叫到屋内。那位看上去像领导的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了。我回答:“我叫拴狗儿,今年16岁了。”“小小年纪,还是去上学吧!”我回答:“我上不起学。”“你爹妈让你当兵吗?”我心酸地说:“我妈死了,后爹后妈都不管我。”此时,邻家一位大叔为我帮腔:“这娃可恓惶呢,肖政委,收下他吧!”“好吧,先留下,看看再说。”
第二天,我随肖政委来到了清源县白石沟。肖政委把我交给了一位姓赵的连长。“把这只‘小狗’先拴在你们连。他还小,要照顾好。”赵连长愣了,“哪里有狗呢?”“他叫时拴狗,这不就是只‘小狗狗’吗?”说的大家都笑了。后来得知,这位赵连长,是八分区四大队三连的连长赵良佐。
连长又把我交给了三排。排长常大臭每天带领我们在西山的涧沟一带活动。常大臭其名不雅,但非等闲之辈。他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小日本一听到大臭这个名字,都吓得失魂落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立了不少战功。后来,他的名字改为常映光了。据说,后来他当了军长了。
1945年春,我们排在一支队马乐清参谋长的指挥下,在清太徐平川开展对敌斗争。这一天,我们来到柳湾村,马参谋长得到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驻孟封村的日伪军要通过南安渡口回清源县城。马参谋长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他马上做了战斗部署,命令我们排星夜急行军向北越过潇河到了西柳林庄。这把我们搞糊涂了。从柳湾村到南安村应当向南走,怎么向北开去?后来才明白过来,这是声东击西之计。有意做出撤退的架势,迷糊敌人,引诱日伪军上钩。急行军七八十里。第二天凌晨,我们折返到南安村了。马参谋长和常排长命令我们找有利地形埋伏起来。大约七点多钟,日本顾问渡边龟带领着约60多人,出现在南安渡口附近。渡边龟是一名非常狡猾的家伙。他怕八路军设伏,于是,派出了侦查哨探路,确信没有八路军时,才将部队开到河边。日伪军一边脱鞋脱裤,一边鬼头鬼脑地四处张望,胆战心惊地下水了。河水很冷,水流很急,越往前走,水越深。不识水性的伪军在水中乱作一团。渡边龟挥着指挥刀命令快点渡河。此刻,只听“叭叭叭”一阵枪响,有几个伪军应声倒在水中。瞬间,日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渡边龟这时慌了手脚,气急败坏地举起战刀,声嘶力竭地喊:“冲过去,快给我冲过去!”正当他气急败坏地在那里指挥时,被我们排的神枪手刘计银“叭”的一枪撂倒了。失去指挥的伪军,在水中打转转。在我们“缴枪不杀”的喊话声中,伪军纷纷举手投降了。
仅仅20多分钟的伏击战,打得非常漂亮。打死了日本顾问及十几名伪军,俘虏了40多名伪军,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其中一挺轻机枪。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常排长让我扛上了。之后我就成为王寿儿机枪班的一名副机枪手了。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全面大反攻阶段。为了配合新的形势,晋绥八分区的党政军编制,作了一些调整,选调一支队副参谋长马乐清任清太徐平川对敌斗争委员会主任,并由马主任带一支队三连三排开展平川工作。三排的排长还是常大臭同志。
这一年初夏,马主任、常大臭同志正带领我们排在太原县洛阳村进行休整、扩军。一天,马主任突然接到地下情报员送来的鸡毛信:驻太原市的日军,对北格镇等地守军被歼十分恼火,拟派特种宪兵队20多人,从小店镇出发,经流涧村进犯北格!对此突如其来的情况,身经百战的第一线指挥员,也同样感到吃惊。
下午,装备精良的23名日本军官和老兵在一翻译的带领下,进入到我们布好的伏击圈内。马主任一声令下,我配合班长王寿儿打出一梭子子弹,六七名日军应声倒下。我又递上了一个压满子弹的弹匣,接过空梭装填子弹。王班长的机枪不断地吐着火舌,一时打得鬼子抬不起头来。敌人端着刺刀冲上来了,英勇无比的常大臭排长带领全排战士,冲入敌群,真是杀声惊天动地,刀光寒气逼人,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马主任带领40多名新兵撤退,日本鬼子罪恶的子弹一股劲儿地向手无寸铁的新兵射击,还没有接触过钢枪,没有穿上军装的小青年,就这样惨死在鬼子的枪弹下。与我们拼杀的几个鬼子,大部分都被我们干掉了。有三名狡猾的家伙,乘乱砍乱杀之际,退到了附近的一片坟地。此时,八班长牛全锁带领几名战士顺着一尺多高的麦苗垅背匍匐前进,接近坟包,他们几个人刚一抬头,即中弹牺牲了。马主任眼睁睁地看着40多名新兵和部分战士的牺牲,气愤极了,命令机枪班长王寿儿射击掩护,他要冲向敌人。但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肩膀,他负了重伤。我们班长气得两眼冒火,刚拉动枪栓,也被敌人击中要害,牺牲了。我见势不妙,接过王班长的机枪,一连打了几个滚,滚到了渠当中,躲过了一劫。马主任满腔怒火在燃烧。在一名战士的掩护下,退出战斗前还大声对常排长下令:“大臭啊,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惨烈的战斗又进行了一会儿,十班长马东娃也牺牲了……
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我们打死了20余名日本鬼子,有力地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然而,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马乐清主任身负重伤,与我共同战斗的王寿儿及牛金锁、马东娃三位班长和包括40多名新同志在内的70多名战友英勇牺牲。
回到清源白石沟后,赵良佐连长派我到交城山上的十五团教导队集训。从此,我离开了曾经战斗生活了一年多的英雄连队,离开了身经百战的杀敌英雄赵良佐连长。谁知,这成了我与赵连长的最后一别。赵连长于1945年4月率领三连突击队,向狐佛山日军据点攻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了。
我在交城山上的十五团教导队集训三个月后,我当上了班长,但我没有下班,而是给我们团长张九德当了警卫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我们十五团改编为交(城)文(水)支队,即五十团,转战在交城山上,与阎锡山勾子军的战斗,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1947年10月,我团在交城县开栅镇的峪口一带驻防。11日,我团的直属九连奉命开赴交城的元宝山执行任务。九连出发不久,勾子军69师的一部突然向我驻守的山头发起进攻。当时团长指挥的部队只有四大员:警卫员,通讯员,卫生员和炊事员。我们几人集中了几支冲锋枪和十几枚手榴弹,一边打一边掩护团长转移。这时,通讯员小张喊着:“团长,敌人从西边攻上来了!”这一喊不要紧,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对手里有一名团长。遂及用小钢炮打过来。第一发炮弹在我与团长的附近炸响后,我知道第二发炮弹会马上袭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向后倒退一步,将团长按倒在地,爬在了团长的背上,一发炮弹就在我们身边炸响了。团长安然无恙,我却受了重伤,—弹片击穿脊背,打进了肺部。张团长听到远处传来枪声,他不知是敌人的增援部队打来了,还是九连的同志们折返回来了。张团长见我背部直淌鲜血,命令身边的这几名同志,要坚决阻击敌人,掩护我俩转移。团长向身边的同志要过一支冲锋枪和两颗手榴弹,背起我向山下撤退。他背着我,在没有路的山间颠簸着。我苏醒后,曾请求他放下我撤退,但团长坚决不依。我们撤退到一个叫“韭菜沟”的地方。团长找到一个农民避雨的土洞,把我放进洞里,把冲锋枪、手榴弹留给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如敌人来了……”我少气无力地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你放心地走吧!”张团长安慰道:“我会让同志们找到你的。”团长要用玉米秸堵住洞口。我这时却像下命令似的:“团长,你不要管我,快离开这里!”我想站起来送别团长,但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含着眼泪,迷迷糊糊地看着团长离去……我又昏迷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我已躺在了兴县蔡家崖的根据地医院。后来得知,九连的同志们听到枪声,知道山上有情况返回来,把敌人打退了。赵团长派了一个排的兵力,把我找到,由卫生员丁喜奎作了应急包扎并带上急救药,再由十几名身强力壮的同志用担架日夜兼程地把我送到根据地医院。几天之后,张团长和他妻子来医院看我。他们带来了一罐子鸡汤。原来是团长的妻子把自己喂养的鸡杀了,给我熬的。这让我很受感动。经医护人员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的伤好了。但是,胸脯常疼,腰也直不起来。此后,我一直留在团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8年在攻克临汾战役时,我团没有直接参战,驻守汾阳、孝义一带,阻击守城匪军逃窜,抵御匪军由太原增援。晋中战役胜利后,我团直插到太原县古城营一带,为解放太原做着准备。我的肺部一直疼痛,咳嗽不止。张团长让我退伍了。经诊断,评为二等残疾。至今弹片还留在肺部,无法取出。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张九德团移师西北,在内蒙古卓资山一带,重创傅作义部,为解放大西北立下战功。抗美援朝时张九德首长,任二十一师师长,后任第七军军长。我回到久别的故乡——东罗村,随后曾在扶贫协会、党支部、生产大队任职。在工作中,我保持了革命军人的本色,起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经常应邀给学生们、民兵们讲战斗故事。我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不要忘记过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