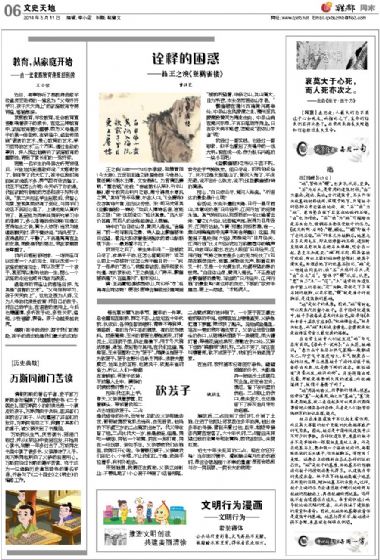每当草长莺飞的季节,童年的一件事,总会重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秋收后,各种庄稼的秸杆,都舍不得烧掉,铡碎后,有的当作牛羊的饲草,有的沤作肥料。就连高粱、玉米的根茬也要刨起来,打掉泥土,运回院子里,码在屋檐下,用于冬天烧炕取暖、煮饭,做到物尽其用。在我们这里,高粱茬、玉米茬都称之为“茇子”,用镢头刨茇子为砍茇子。茇子在野外经秋冬两季,须根大都腐烂,地面上的茎杆,也被风干,砍起来省时省力,所以,人们一般都在春耕前,将茇子砍掉,不然犁入土中,清除的时候就费时费力了。
那年我还未上学。春天,父亲挑着箩筐,扛着镢头,带领着我和二占去地里砍茇子。二占是我姑母的孙子。他爷爷、奶奶及父亲相继去世,哥哥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杳无音讯,他妈扔下不满三岁的二占离家出走了。我父母收留了他。二占比我大一岁,虽是叔侄,但是,同吃一锅饭,同钻一个被窝,同在一起打闹,同在一处玩耍,亲如手足。父亲要领我们去地里,我俩可开心啦。争着要扛镢子,父亲嫌我们年纪小,个子矮,不让我们扛。于是,我俩手拉着手,向村外跑去。
来到地里,我俩还在疯跑,父亲立刻制止:不要乱跑了!小心茇子绊倒了!话音刚落,二占竟然真的被绊倒了,一个茇子茬正戳在他前额的中间。他爬在地上哇哇直哭,父亲急忙撂下箩筐,把他扶了起来。见他满脸是血,站在一旁的我吓得也哭了。父亲让他按住额头的伤口,从破棉袄里撕下一块棉花,用火镰打着,等棉花烧成黑灰,便敷在伤口处,又解下他的“裤脚带”绑扎好。二占不哭了,可还在叫嚷着疼。砍不成茇子了,我们扫兴地返回了家。
在当时,农村基本没有医疗条件。磕磕碰碰的外伤,大都是弄一把细沙土或棉花灰止血。往往会发炎、溃烂,留下很明显的伤疤。二占额上的伤口,虽未发炎,也还是留下了深灰色月牙形的疤痕。
解放后,二占回到了他们村,分到了土地,住进了他那让邻家居住多年的房。他出走多年的母亲,曾回来看过他,后来,他随母亲去内蒙古定居了。六十年代时,二占曾回来探望过他的老舅爷和老舅妈,因我在部队,未曾见面。
近七十年未见面的二占,现在你还好吗?当你面对镜子,看到额头弯月形的伤痕时,是否会想起那个不幸的遭遇?是否会想起与你一同玩耍、一同长大的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