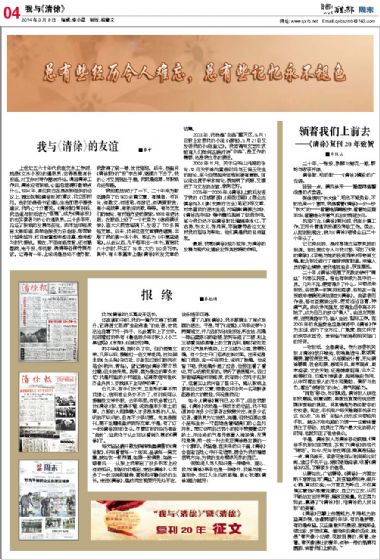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文水工作时,就是《文水小报》的通讯员,觉得县里有份报纸,对工作对写作都有好处。调回清徐工作后,清徐没有报纸,心里总觉得好象缺点什么。1994年,有位同志在县政协组织的会议上,提出恢复《清徐报》的建议,我立即附和。当时的县委书记阎沁生当即表示接受建议,我内心十分喜悦。《清徐报》复刊后,我迅速与报纸结为“连理”,成为《清徐报》的忠实读者与热心的通讯员。二十多年来,见证了报纸的发展与变化,由本地印刷改到太原印刷,由单色报变为彩色版,版面设计越来越好,栏目设置愈来愈丰富,愈来愈与时代接轨。现在,不但有纸质报,还有醋都网、电子报、手机报、微博等各种传媒形式。记得有一年,上级说是县级不准办报,我像得了病一样,恍恍惚惚。后来,县里将《清徐报》的“报”字去掉,继续办下去了,我的心才又回到肚子里。我就是这样,与报纸命运相连。
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二十年来为报纸提供了近500余篇文章,有消息、有议论、有散文、有随笔、有游记、有调查报告、有小说故事、有新旧词歌,等等。有与文友们的辩论,有对地方史的探索。1998年退休后,在报纸上设了一个栏目为《休闲清谈录》,在太义同志编辑下,发表了100多篇短文章。后来,我将这些文章鳞选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书,取名为《中庸堂随笔》。从此以后,几乎每年出一本书,直到我八十岁时,共出了16本,大约160多万字。其中,有6本基本上是《清徐》所发文章的结集。
2003年,我县是“非典”重灾区,5月1日报上发表我的小说《避难》,5月21日又发表我的小说《登记》。我觉得用文艺形式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对待“非典”,是工作的需要,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2004年11月,关于马鸣山问题的争论,12月关于徐沟置县时间与王保玉先生的辩论,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很有意思。可以说这属于学术辩论,既辩明了问题,又增进了与文友的友谊,非常之好。
2005年—2006年,《清徐》上前后发表了我的《红楼絮语》、《闲话红研》、《商业古镇徐沟》、《读〈太原府志全〉笔记》等文章,对丰富我的退休生活,对编撰《清源古城》、《清徐古寺庙》等书籍均起到了促进作用。至今我仍然不忘清徐报社编辑李永红、丁志勇、张太义、张月英、李晓霞等各位文友对我的指导与帮助,他们真是我的良师益友。
最后,我愿《清徐》越办越好,为清徐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发挥其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