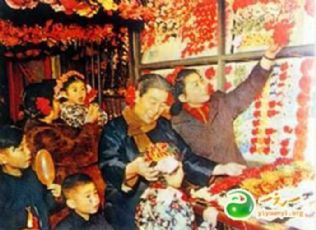从记事起,我已经度过50多个春节了。记忆中的春节,有甜蜜、有苦涩、有喜悦、有悲伤,但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75年的那个春节。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几乎所有的传统习俗都被当作“四旧”破除了。农村的祠堂、庙宇、神像、牌位等“封建迷信”的东西,基本上被红卫兵毁坏了。连秧歌、皮影、舞龙舞狮也不能上演了。当时实行“五不准”:即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赌博、不准大吃大喝、不准演古装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过春节的形式也大为“革命化”。
我是1973年7月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的。并于当年12月入党,进入大队领导班子,担任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等职。我所在的村是个先进生产大队,又是公社所在地,因此,各项工作都不能落后。1975年冬,是我任职的第3年。我记得,为了让全村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根据上级安排,大队党支部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支委们分了工。我的任务是搞好宣传和妇女工作,蹲点第3生产队。
为了使年轻的一代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热爱新社会。年三十晚上,我们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每个小队至少派20个年轻人参加。在大队会议室,凡参加会议的人,先吃忆苦饭。忆苦饭是用白菜邦、胡萝卜、米糠、玉米面煮成的粥,粗糙难咽。然后,让解放前苦大仇深的两位老贫农代表,诉说他们在旧社会出得牛马力,吃得猪狗食的生活,说到痛心处,老人竟痛哭流涕,使在坐的年轻人深受教育。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大家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与其它语录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并高喊政治口号,声音响彻夜空。开完忆苦思甜大会,人们才可以回到家里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晨,我吃罢饺子,便匆匆忙忙赶到大队,打开大喇叭又开始宣传。“社员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是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我们要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移风易俗过春节……”早饭后,全村的社员都拿着劳动工具纷纷跑出来,等待生产队长分配任务,生怕迟到了挨训。说句良心话,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好不容易盼来个春节,谁不想在家里暖暖和和、团团圆圆过个年嘞?可是小腿拗不过大腿,干部的话就是圣旨,无人敢对抗。农村的冬天,天寒地冻,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但是,为了展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展现人们高昂的革命热情,体现“革命化”的春节,村干部们还是能想出不少办法。我广播完之后,急忙赶到第3队。只见队长带着一些青年社员己开始担水、翻粪堆(每年秋收后,各队都要把玉米秆和高粱秆切碎,让下山的羊群踩圈,加上饲养院的牛马粪便与积来的其它东西,组成一个大粪堆,为来年地里的主要肥料)。副队长带几个壮劳力,在饲养院出圈。政治队长带女社员和知青,在辖区的村内外积肥。我找了把铁锹也与他们一起劳动。当时,全村男女老少齐出动,大搞积肥沤肥。大家不怕寒冷,不怕泥水,挥汗大干,还唱语录歌,大有气吞山河的气势。
午饭后2点多,由我主要负责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在我大队露天剧场正式开始。锣鼓响起来,乡亲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向剧场。演出的节目有:小合唱、独唱、表演唱、快板、乐器合奏、舞蹈、歌剧、样板戏(节选)。那时候,旧戏不准演,说什么要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新戏只有8个样板戏,整演一部,我们下不来,只能节选几场。另外,就是发动群众,自编自演。我还编写了一个叫《喜日子》的小歌剧,经我村老团支部书记赵受祥修改后,竟然还参加了公社、县里的汇演呢!演员和乐队成员,主要是本村的文艺骨干、一些在校回乡过年的大中专学生和部分知青,共70多人。大家都是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相当辛苦,无报酬,无怨言。只要有演出任务,都积极参加,并取得较好的成绩,为村里争了光。
那时,对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的语言不见了,内容也非常的“革命化”。例如:“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战天斗地过大年,政治挂帅立新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人们贴得年画,基本上是毛主席画像、样板戏人物或战斗英雄画像。
往事如烟,转眼己过去39年了。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些都是不可思义的。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多数人是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