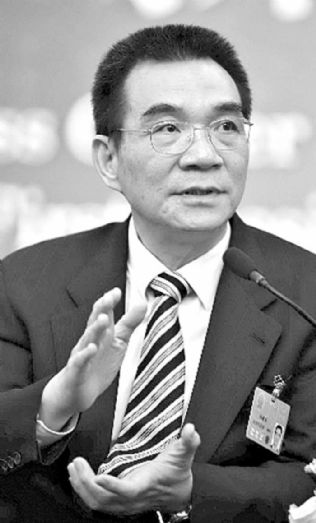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到大陆后改名),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根据汉语大辞典,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可代代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宗师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
一个文化体,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会形成一个自洽的实体。当生产力水平很低时,公社的组织方式有利于发挥打猎时的规模经济,共有共享的伦理价值则有利于克服因为生产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储存给每个人生存带来的风险。所以,这种组织方式、价值伦理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洽的。后来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猎进入到农耕,由以石头为工具进入到以铜器、铁器为工具,组织的方式则演进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伦理、价值由原来的共有变为私有,这种演变归因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的实践中,每个文化体都会是器物、组织、价值三个层次自洽的实体。
文化复兴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的文化里面,有什么是绵延不断的呢?当然是它的伦理、价值绵延不断,因为工具和组织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文化三个层次中的经济基础来看,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普遍认同,中国在宋朝曾经有一段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组织的层次看,周朝时为井田制,为近似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秦汉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明朝初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组织与生产关系,中国的经济组织方式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因此,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从没有变过。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这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第一,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
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20年甚至30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低,外国很多著名大公司的主要骨干科研人员都是中国人。
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
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当时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21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
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二十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
由此可知,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
再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
如果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上,但实际上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也并非绝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在从小与父母和周围人的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榜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绝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
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受到冲击。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