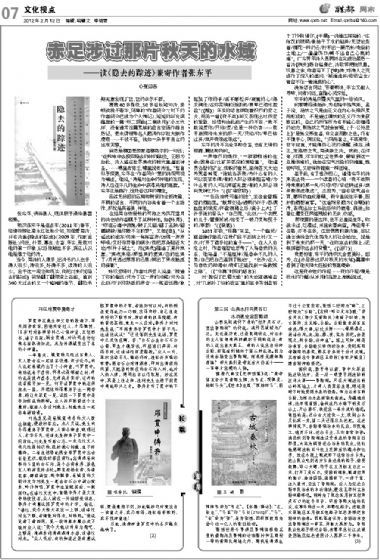◆张卯春
张东平,清徐县人,现供职于清徐县国税局。
初识张东平是在去年(2011年)春节,经清徐报社李永红社长介绍,知他爱写诗,并有诗集《隐去的踪迹》(2009年,作家出版社)问世。朴素、寡言、含蓄、平实,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以后接触也不多,真正认识他是缘于他的诗。
当今,写诗的人很多,出诗书的人也多,诗人很少;诗很多,好诗不多,读诗的人很少。出于这一观念和现实,我把讨来的《隐去的踪迹》简单翻了翻便束之高阁。直到360天过去的又一个喧闹的春节,翻捡书架无意发现了它,它的卓尔不群。
薄薄40多张纸,30多首长短句诗,装帧淡雅不奢华,简单的“作者简介”(时下的作者简介已成为个人传记),短短的却充满蕴意的一篇“听二胡曲《二泉映月》”小文代序,没有通常连篇累牍的虚言空话作前言后记,更未请领导名人题词作序拉大旗作虎皮……不枝不蔓,犹如一朵亭亭玉立的出水芙蓉。
扉页是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去的神的踪迹。正因为如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出神圣。……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哲言似乎深奥,东平在“作者简介”里的诗观可视为阐述。他说,“诗是对生命的神性的发现,诗人应在平凡的生命中获得灵魂的高度。”东平正是践行、诠释着这样的理念。
品读无标题的五辑和附录的全部诗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内容共有着一个主旋律,那就是真善美,神性。
在描写自然景物的可称之为风花雪月的诗也被作者赋予了某种神性。如《咏月》,“你在云海中流浪/缺了又圆/圆了还缺/圆圆缺缺/是你做不完的梦”。又如《春》,“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阵阵雷声/仿佛一声声呼唤/又好似青春的脚步/我把耳朵贴近大地/听种子破土”。而《黑夜》蕴涵了某种寓意:“黑夜来临/那些黑的更黑/白的也黑了/月光透过厚厚的云层/照出了黑夜魅惑的身影”。
咏叹爱情时,作者对所爱人说道:“拨通了你的电话/只为了这一声的问候/只为在此刻/听到你熟悉的声音……握着话筒/象握紧了你的手/再不愿松开/寂寞的心/渴求润泽/在你柔情的话语间/我早已泪水盈盈”(《赠》)平实的语言燃烧着炽烈的爱之火,而另一首《我不敢》却又表现出对所爱的崇敬、珍惜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安:“我不敢说爱你/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我不敢期待未来的那一天/只怕/你/早已转过身/离开我很远很远”。
东平的诗不完全平和含蓄,也有无情的揭露、鞭挞和拷问。
一声惨烈的爆炸,“一群群鲜活的生命/葬身在/比矿井更深的黑暗里”。他谴责贪婪的矿主、渎职的官员,面向苍天大地为死者喊冤:“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安享幸福/有的人却必须承担苦难/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挥霍无度/有的人却必须向死神乞怜?”(《矿难悲歌》)
“一张张油光可鉴的脸”,坐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觥筹交错/透明的杯子/斟满血红的琼浆/杯盘狼藉之后/桌子上/吐了许多谁的骨头?”自己呢,“此刻/一个农民的儿子/置身其间/饱受了一顿刀叉和筷子的/宰割!”(《豪宴》)2003年初,“非典”突至。“一个幽灵/露着狰狞面孔/在我们猝不及防之时/又一次/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人人自危之时,作者理智地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写道:“不是瘟神/是自命不凡的人类/自己把自己逼到了绝地”。“也许/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我们还能找到一条救赎之路”。(《“非典”时期的感言》)
对“撕裂了巴蜀大地”的大地震遇难者,对“几间补丁似的教室”里的孩子等弱者寄予了怜悯情怀。《干旱》一诗是这样写的:“庄稼汉的眼睛/象抽干了水的枯井/无望地张着/棉花一样的云/拧不出一滴雨来/龟裂的土地上/一道道伤口/喊不出自己心底的痛”。广东青年诗人吾同树在完成他最后一首诗《消失》后自缢身亡,诗歌界扼腕叹息。叹息之余,作者写下了《悼》诗,对诗人之死进行了深入的追问:“被谁遗弃/茫茫尘世/竟留不住一颗纯真的心”。
诗集语言简洁,节奏明快,平实又耐人寻味,间有问话,直指心灵深处。
东平的诗是阴霾天气里的一缕清风。
问君哪得清如许,为有胸中浩气来。孟子说,浩然之气是由正义在内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不是通过偶然的正义行为来获取它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不能心安理得的地方,则浩然之气就会衰竭。(子·公孙丑上》“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简而言之,不慕荣华,甘守寂寞,才能保持心灵的清醒、清高、清正,发浩然之气,写清新之诗。然而,在浮夸、浮躁、浮华的红尘世界中,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犹如在空气污染的环境里,既要呼吸,又要保持健康一样困难。
基于此,有了些许担心。谨借东平的诗来表达我——一个读者的心情:“我不敢期待未来的那一天/只怕/你/早已转过身/离开我很远很远”。还因为,“曾有豪气逼云霄,愿将热血化春潮。而今羞说生平事,围炉酌酒慰寂寥。”这首附录题为《自嘲》的诗,表现出如士兵战后似的疲惫、孤独;如春红遭受狂风摧残般的无奈、伤感。
即使真的是这样,也不必羞说生平。你战斗过,烂漫过,并且余香尚留。诗在骨不在格,亦不在多。这册薄薄的新诗集,足以确立清徐当代优秀诗人的社会地位。就是到了未来的那一天,“在你离去的路上/还凝固着你远去的背景”。(《送行》)
我更相信,东平的诗明天会更美好。因为,在《赤足涉过那片秋天的水域》篇章中看到了他天降大任般的崇高使命:
这是我命定的行程……我的行程/便是秋水的行程/从岁月的高原上/蜿蜒流过。